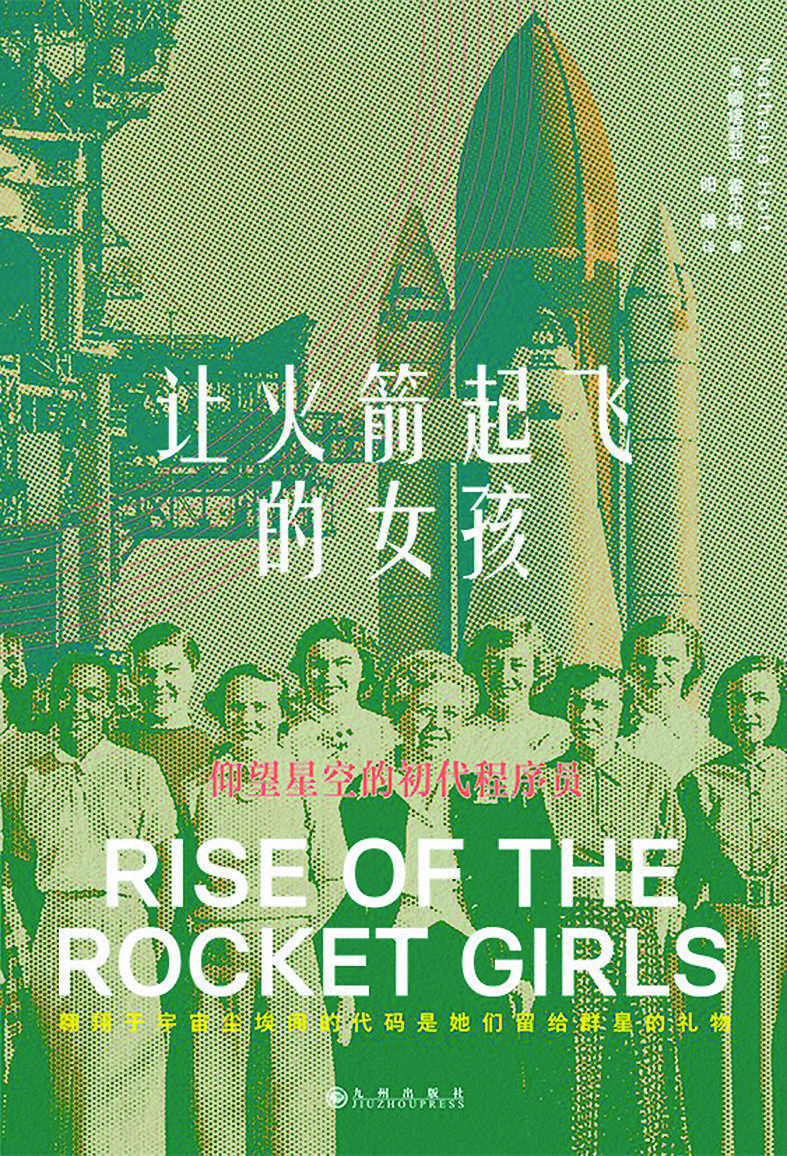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10-06 第28105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意想不到的职业女性,殊途同归的自由意志
《持家的人:女性劳动与能源变革》 [英]阿比盖尔·哈里森·摩尔 [加]R.W.桑德威尔 著 李菲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出版
■郭垚“穿越”在当下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故事设定,然而,在一般的女性向作品里,“穿越”后的女性主人公无论拥有何种身份——公主、才女、婢女抑或是绣女、医女、侠女……故事多以家庭为活动轴心,以亲缘与性缘的变动为人生驱动力,描写她们职业生活的笔墨甚少。当然,有部分原因是这些人大半“穿越”到了古代,可描写的空间狭窄。不过,即便“穿越”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生产力大发展的工业时代,人们对妇女的职业想象依旧贫瘠,停留在家庭教师、文职秘书、纺织女工等有限的职业身份上。
设若有一位作家要积累素材,描写以职业生活为主体的“穿越女”的故事,他该如何取材呢?以下这几本著作,或许可为撰写职业女性故事提供启发。
消费赋权——家庭内部决策如何影响能源市场
只将目光聚焦在传统职业上,势必无法推陈出新。要将视野放大,先从不够为人熟知的职业入手。阿比盖尔·哈里森·摩尔的这本《持家的人:女性劳动与能源变革》就提供了新的思路。它向读者介绍了艾格尼斯·加勒特和罗达·加勒特姐妹这对专业装潢咨询师。她们是英国首家全女性设计和装潢公司的创始者,在1877年出版了《家庭装潢建议》,直接面向女性读者。
19世纪60年代以前,家庭装潢决策主要是男性作出的,那时候家里的一切决策都以男性为主导。到了19世纪70年代,像加勒特姐妹这样的职业女性试图推动女性在家庭装潢中的决策权,利用消费决策权提升家庭话语权。她们面向中产阶级,提供了“一套简单的、不花太多钱就能让家居环境更美、更健康的方法”,并辅助客户买入先进的燃气或电力设备。另一位从事相关研究的女性霍伊斯夫人在两姐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她竭力推广更安全、便捷的电灯——当时英国家庭广泛使用的蜡烛和煤油灯安全隐患极大。她呼吁女性创造符合自己价值观念和品味的家,在装潢师的辅助下行使自己的家庭管理权。
在燃气和电力公司的市场竞争中,女性在说服消费者在家中作出能源决策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像女性电气协会这样的组织更为电力技术的推广作出了卓越贡献。有成百上千位指导、推广和示范用电的女性电气协会工作人员持续付出,提升数百万房主对于家庭电力消费的认知。这其中,身为协会干事、《女性工程师》编辑的卡洛琳·哈斯利特正是另一位职业样板。她不仅挖掘了独立电气工程师玛格丽特·帕特里奇,更积极介入政治,为女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家庭能源的变革,不仅造就了与之相关的职业女性,更为普通家庭主妇带来新的观念:家庭内部的许多工作和决策都具备社会价值,劳动方式和社会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每个人的每个选择都在影响世界。
在现下这样一个生产过剩的年代,人人都在互相提醒不要走进消费主义陷阱。然而将时钟拨回到19世纪末,英国女性还没有完全获得选举权。她们通过消费获得的一点话语权是撬动现状、争取社会地位的途径之一。尽管家庭装潢、能源选择等决策看起来琐碎、不值一提,可英国的已婚妇女却从中逐渐建立起独立掌控财产、行使决策的意识。像加勒特姐妹这种针对女性用户群体的职业女性,也有了充分发挥能量的舞台,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新兴职业女性,英国女性正是依靠这一点一点微小的权力争取,最终赢得了财产平等、人格独立。
自我学习——单调的劳动如何引起知识质变
如果说消费赋权观具有一定争议,那么这本《玻璃底片上的宇宙:哈佛天文台与测量星星的女士》在女性职业介绍方面则显得更为“纯粹”。书中记录了不少“天文观测女工”的故事,她们所做的工作看似简单:每天晚上观测恒星的亮度变化并记录下来,不需花费什么力气。然而实际上,观测任务十分繁重,要确定任何一颗变星(即可变的恒星)的光周期,都需要进行成千上万次观测。有时,一个晚上就要进行900次测量。测量后,拍摄下来的玻璃底片也需要整理,再运用公式进行计算。
从事这份工作的弗莱明太太的上一份职业是女佣。她七岁丧父,后来与丈夫詹姆斯·奥尔·弗莱明结婚,移民美国,但很快丈夫抛下怀有身孕的她消失了,她只好出门找了一份女佣工作。可能因为过去在苏格兰做过教师,她很快被雇主——哈佛天文台的爱德华·皮克林的太太推荐给丈夫,做了天文台的抄写员和计算员。通过一段时间的实地工作,弗莱明太太的观测技术逐渐升级。开始,她只是进行记录,并使用皮克林给出的公式计算恒星的星等,后来,她学会了看夫琅和费谱线,并且能够从玻璃底片上的星域中判断出星等来。
1890年,在工作了近十年后,她在哈佛天文台《纪事》的第二十七卷发表了《德雷伯恒星光谱星表》。1891年,她在海豚座发现了一颗新变星,自此探测新的变星成为她的强项。而她的辨别方法,正是从长年累月的观测和记录中总结而来。
弗莱明太太的成功不出意外地招来了争议。赛思·卡洛·钱德勒就曾在自己发布的星表中忽略她的几乎所有的最新发现,在一个附录中,他还将她发现的十几颗变星描述为“据称如此但未被证实”,因为他对哈佛天文台的观测方法持保留意见。不过这样的敌意并未持续到最后,1898年,一颗新的小行星出现,为了测算位置,钱德勒不得不向哈佛天文台求助,寻得他们的拍摄记录。弗莱明太太从十万张库存中挑选出最有可能的照片,花了好几个月梳理,最终在1899年找到了钱德勒要找的那颗小行星的影像资料。这颗促成科学共识的小行星,正是大名鼎鼎的爱神星(Eros)。
同样是1899年,曾经的女佣弗莱明太太,被哈佛董事会正式任命为新设立的天文照片馆馆长,42岁的她,是首位在天文台、学院乃至整个大学拥有头衔的女性。此后,弗莱明太太愈发勤奋,她的《变星的一种照相研究法》,给出了3000多颗恒星的位置和星等,它们都曾被用于追踪她发现的200多颗变星。从一开始单调乏味的辅助性工作到后来独具慧眼的创造性工作,弗莱明太太完成了艰苦而又快乐的自我学习,再次证明了一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自我教育。不过略显遗憾的是,全书大部分都称呼她为弗莱明太太,只在一个地方记录了,她称呼自己为米娜·弗莱明。
突破舒适——不一样的选择如何助力重塑自我
无独有偶,娜塔莉亚·霍尔特的《让火箭起飞的女孩:仰望星空的初代程序员》一书也记载了一群从事基础工作的职业女性。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雇佣了450位计算员,其中有76名女性。而在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却汇聚了一支富有数学天赋,几乎全是女性的计算员团队,她们用智慧的劳动,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火箭升空,这是相当难得的。要知道,在1960年的美国,有工作的妈妈是一种稀有动物:孩子不满18岁的美国已婚女性里只有25%的人会去上班。更可贵的是,随着时代发展,计算技术进步,这些计算员女孩没有因为躲在舒适区而被职场淘汰,而是直面挑战,学习新的技术,逐渐变成NASA的第一批计算机程序员。在技术不断革新的年代,她们需要经常学习新设备的使用方法、新的计算机编程语言。技术问题没能阻挡实验室女孩们的升级之路,到70年代时,实验室90%的编程工作都由她们负责。彼时,有些大学的工程系刚刚开始招收女学生,而JPL的女雇员们却已经完成了从计算员到工程师的转型。
能够保证她们坚定开展职业人生的因素,除了这些女孩自身的坚持,团体互助的氛围也必不可少。JPL团队几乎所有女性都遭遇了生育期困境。在怀孕期间,出于种种考虑,她们总是不得不在继续就职和辞职回家中做选择。即使是身为主管的芭芭拉·鲍尔森,也不能免除这样的命运。好在同样身为女性管理者的海伦·凌没有忘记自己的伙伴,在芭芭拉生育后,邀请她回到实验室。JPL愿意为妈妈们做一些妥协,给她们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时间。同样是生育后回到工作岗位的苏·芬利甚至逐渐治好了自己的焦虑症——这一点在如今恐怕不一定能得到理解,因为当下很少有人会真心实意地表达“工作让我快乐”。然而在上世纪,工作,真的能改变一些女人的生活,让她们换一种活法。
或许这种群体聚力的职业有“圈地自萌”的嫌疑,那么霍普·洁伦的自传《实验室女孩》可以给出更为具体、更为个体的职业参考。三获富布赖特奖、斩获两枚地球科学领域青年研究者奖章的她,是一名地球生物学家。因幸运地生于20世纪中后期,她与上述女性相比,拥有更广阔的职业道路。尽管如此,在明尼苏达大学念本科时,她每周都工作20小时,打过十种不同的工,因为有些东西必须要亲自体验。她认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不做别人安排好的实验,她会设计自己的实验,从中获得全新的知识。”在她的人生叙述中,穿插了各类植物的生长知识,她像自己所研究的植物一样愿意面对困难:“如果一件事能不经历失败就获得成功,那么早就有人达成了,我们也没必要费力气。”
之所以认为这四本书可以为作家提供原型参考,是因为它们将女性的职业生活具体化、可视化了。当人们谈起职业女性,不能只停留在“呼吁大家都要走出家庭,从事社会工作”的口号阶段,而是要用实际案例展现历史上职业女性的机会在哪里,她们是如何不断学习、不断成长、不断收获的。这些人所处的时代、出身境遇和所选道路虽不同,却拥有共同的生命内核:生命由自己决断,不自我设限。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诚然我们无法摆脱天赋、出身、时代加诸己身的隐形围栏,但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拥有自由意志,可以参与自身命运的建构。这些与众不同的职业女性的人生故事,依然可以带给当今的我们以启发和激励: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吧,在那之后,重塑自己、成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