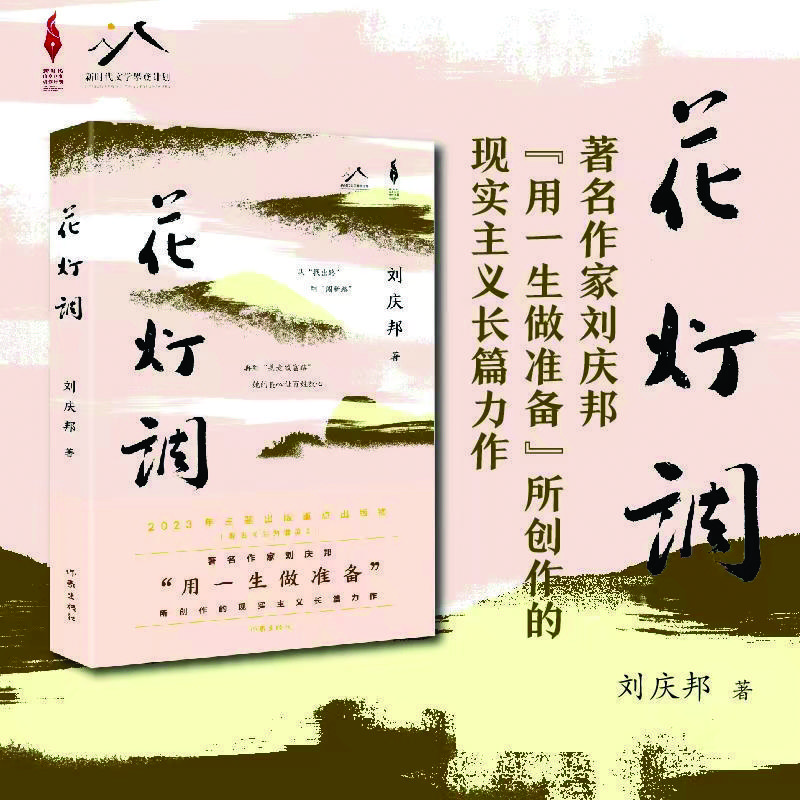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03-19 第27,904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大半生的充分准备,书写新时代的中国美
——关于刘庆邦长篇小说《花灯调》的对话
刘庆邦创作的长篇小说《花灯调》聚焦贵州高海拔贫困山区的高远村,来自市区检察院的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带领干部和村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实现了全面脱贫。
对话嘉宾 刘庆邦(作家)王雪瑛(本报记者)刘庆邦创作的长篇小说《花灯调》首发于《人民文学》2023第11期,《小说月报》2024年第2期转载,2024年新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花灯调》聚焦贵州高海拔贫困山区的高远村,来自市区检察院的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带领干部和村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在山地上修建公路、水库、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村民们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实现了全面脱贫。通过嘉宾之间的对话,让读者了解刘庆邦如何发现小说的人物原型,怎样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塑造“时代新人”的形象,展现人们在面对贫困与富裕、传统与现代的发展命题时的观念变化与心灵成长。
长篇小说如大海,短篇小说如瀑布
王雪瑛:您多年来以短篇的有限篇幅书写人生海海,探寻大千世界的人性回响。今后您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还是根据题材需要,创作不同体量的小说?
刘庆邦:写完这部长篇之后,我又连续写了十多个短篇小说。我喜欢写长篇小说,也喜欢写中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是点,中篇小说是线,长篇小说是面。长篇小说如大海,中篇小说如长河,短篇小说如瀑布。长篇小说像太阳,中篇小说像月亮,短篇小说像满天星斗。各种小说体裁各有各的形态,各有各的声音,各有各的光亮,都不可或缺,谁都不能代替谁。
有评论家说过,短篇小说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水准的试金石。拯救文学性要从重新重视短篇小说开始。短篇小说是我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们像是一把把小小的钥匙,帮我打开一个个心灵世界,并再造一个个心灵世界。其实,把诸多短篇小说加起来,形成合集,也可以构成长篇小说的容量,从中也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世界。
王雪瑛:听说最初这部长篇题为《泪为谁流》,为什么后来改为《花灯调》这个更有审美韵致的书名?
刘庆邦:这部长篇一开篇,我起名为《泪为谁流》,直到小说全部完成。女主人公驻村第一书记为脱贫攻坚付出很多,她的眼里常含泪水,为了争取到扶贫项目,为了动员村民参与修路,为了隐瞒自己危险的病情,也是为家人对她的无私支持所感动,她多次泪流满面。她的热泪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是饱满深情的外溢。她的眼泪是为村民而流,为老百姓而流,希望乡亲们能尽快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
我在写作小说的过程中,常常泪眼模糊,看不清字迹。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为书中人物所流,为读者所流,也是为自己所流。
直到《人民文学》将发表小说时,我想来想去,才决定将小说改名为《花灯调》,这样更含蓄,更美丽一些,也更符合整部作品的文学艺术调性。书中多次写到当地广泛流传的花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庆祝活动,村民们就会自发唱起花灯调,歌唱山村的巨大变化。花灯调有独特的地方色彩,更能表达民众心声。
王雪瑛:作为一个生活积累丰厚,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您曾经提到创作《花灯调》是一次特别体验,与以往的创作状态不同,是处于一种忘我的状态?
刘庆邦:我在日记本上记得很清楚,2022年12月18日始,我感染新冠,发烧,咳嗽,嗓子疼,浑身无力不想动。但我的写作雷打不动,照样早上4点起床,投入写作。我每天给自己规定的写作任务是写满五页稿纸,一千五百字。我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不信战胜不了它,意志力战胜一切!小时候,母亲对我很娇惯。成年后,我一点儿都不娇惯自己,用自己用得甚至有些狠。我曾怀疑过自己的写作才华,但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意志力。我的意志力促进和保障了创造力的发挥。
王雪瑛:《花灯调》是您的第十三部长篇,也是第一部叙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长篇小说。不到一年的时间,您就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您说过:“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大半辈子的充分准备,大半年的忘我写作,《花灯调》对于您的创作生涯而言有着什么重要意义?
刘庆邦:仅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我曾经写过六部,这些长篇写的是过去的生活,记忆中的生活;《花灯调》写的是眼下的生活,正在发生的生活。我以前写的农村生活,差不多都是我老家的生活,是“我生活”。这次写的是我国大西南革命老区的山村生活,是“他生活”。从写“我生活”,到写“他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转变,也是一个挑战。我知难而进,有意向自己发出挑战。
我已是年逾古稀的人,原以为自己的激情在衰退,情感会淡漠。经过定点深入生活,了解到那位驻村第一书记的系列事迹后,我的激情又燃烧起来,情感又充沛起来。回到北京后,我的脑子里老是回旋起那位第一书记的形象和事迹。我的心情如此激动,除了为驻村书记的事迹所感动,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有一种紧迫感,自己岁数大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逐渐下降,担心拖得时间长了写不动。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写这部小说特别有意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带来的全面脱贫、步入小康和乡村振兴,我愿意用共同奋斗创造的丰碑来概括。丰碑,不是石碑,是口碑,是建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我必须写出这部作品。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品,读者呼唤这样的作品,如果我不写出来,就对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使命和责任。
在描写具体人物时,认识时代新人的特质
王雪瑛:小说中的人物周志刚说,“我认为你们下来验收高远村的脱贫攻坚成果,既要见物,也要见人”,《花灯调》让读者看到了人物群像。山乡巨变是人干出来的,这是生动描绘脱贫攻坚真实过程的重要环节,众多的人物展开宽阔的社会层面,这很考验作家的功力,是您写作中的难题和挑战?如何评价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其中哪些人物更让您感到满意?
刘庆邦:小说中转业军人周志刚对验收团领导说的话,也是我在写作中对自己的要求。高远村全面脱贫靠的是上下拧成一股绳所形成的合力,《花灯调》塑造的是人物群像,可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正面人物形象,像驻村第一书记、区委书记、镇委书记,还有老支书、村主任、周志刚、刘丽、任欢欢等,都是个性鲜明、各有千秋的正面形象。除了女主人公向家明,我还很欣赏转业军人周志刚,他不仅是脱贫攻坚中的骨干力量,简直就是一位冲锋陷阵的英雄。
写山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不但要写物质的变化,更要写人的变化,写人的观念之变,精神之变,行为之变,形象之变。写好人之变,才能真正全面和深层次表现山乡巨变。另一个层面是比较复杂的人物形象,他们各有各的弱点和毛病,让人欣慰的是,这些人物后来都发生了可喜变化,他们的面貌焕然一新。
王雪瑛:小说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塑造了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如何避免驻村人物概念化,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的“时代新人”形象?您在写作中如何应对这个当代作家面临的课题?
刘庆邦:如何塑造血肉丰满的“时代新人”,正是这部小说的着力点,也正是我常思考,想回答的问题。我每年都回农村老家看看,对老家的变化,我看在眼里,动在心上,很想写一部反映农村现状的长篇小说。有了写作的愿望,还要有写作的机缘。人物形象塑造得是否成功,是一部长篇小说成败的关键。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纲,纲举才能目张。主要人物犹如一棵树的骨干,只有骨干立起来了,才撑得起满树繁花。全国有五十多万个驻村第一书记,他们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我设想,最好能找到一位驻村第一书记为主要人物,才能把所有素材集中起来,统率起来。当我有幸相遇遵义山区这位驻村书记时,心里一明,众里寻“她”千百度,获得过“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的她,正是我要寻找的驻村第一书记的优秀代表人物!她对这部小说的启动作用是决定性的,没有这个人物,就没有这部小说。
正是在塑造新时代新人的用心探索中,在向家明这个具体人物身上,我才逐渐认识到“时代新人”的特质。“时代新人”形象不是一个概念,是通过具体行动在向家明身上体现出来。她不是那种“高大全”式的人物,她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她也想得到职务上的升迁,也想过多挣工资,遇到不开心的事,她也跟丈夫使小性子。她与不同人物打交道时,用不同方法,不同语言,体现出她立体形象的多个侧面。
王雪瑛:中年人的情感面临着现实生活的种种磨砺,向家明离开城市,和丈夫的两地生活中,更显相互理解和支持的珍贵,他是雪中送炭贴心支持的亲人,家里家外风雨同舟的战友,还是理性分析敢于直言的诤友。他让她在砥砺前行中后顾无忧。小说在他们的关系中,深入了向家明的心灵世界,也寄予着您对女性情感的关注,对中年人情感的理想。
刘庆邦:向家明投入脱贫攻坚战役,能取得超预期的成果,丈夫对她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丈夫的支持,不仅有情感,道义,还有智力上的。丈夫帮她出了不少好主意,是她的坚强后盾。一人去攻坚,全家总动员,父母、孩子、妹妹和妹夫们,都支持她的工作。
向家明爱唱歌,爱美,爱小动物,爱动感情,她是一个情感丰富,有激情的女性,她不是“方海珍”,不是“江水英”,也不是“柯湘”,是不可复制的“这一个”。她在工作中的果敢决断表现出“女强人”的一面,但她不失是有平常心的女儿家,她的心灵还是温柔善感的女性世界。她是人到中年,但依然保持着朝气蓬勃的劲头。
评论家李敬泽在评论我的作品时说,川端康成写的是日本美,刘庆邦写的是中国美。敬泽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为我的小说创作指出了一个方向,他的评价让我深受鼓舞。我也喜欢川端康成的一些小说,我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部《花灯调》,是我努力写出新时代的中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