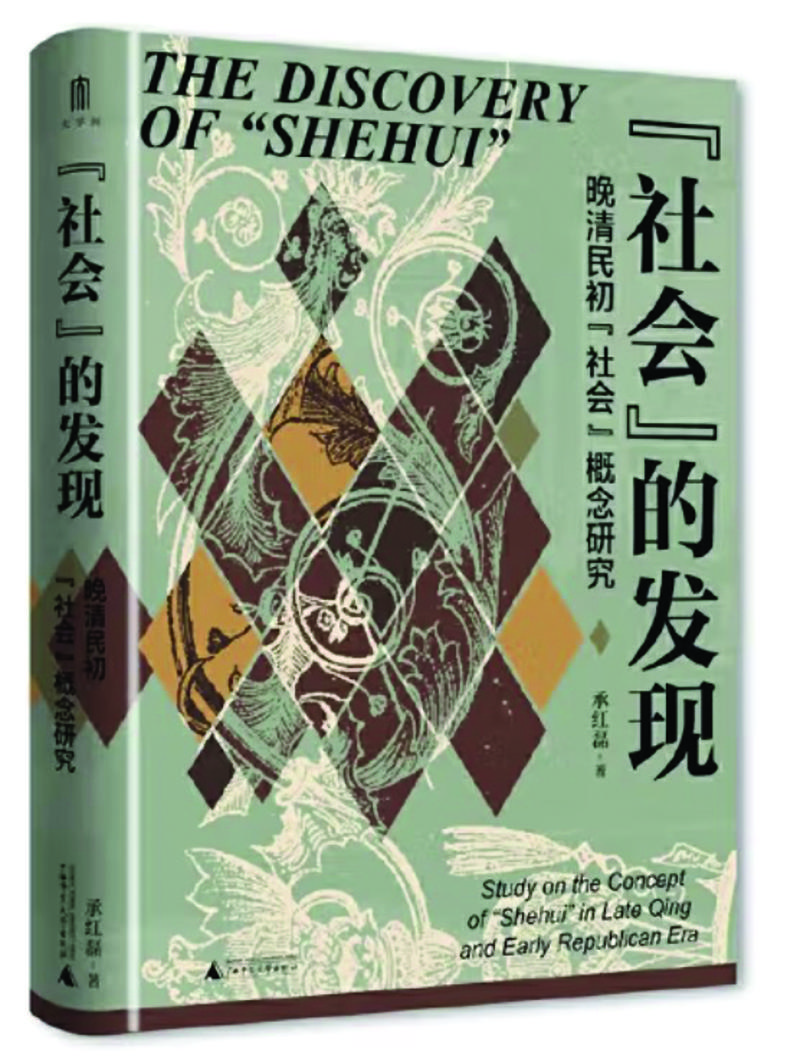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03-17 第27,902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从“社会”的传入看近代中国变迁
——读《“社会”的发现》
《“社会”的发现∶晚清民初“社会”概念研究》 承红磊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贾登荣从1895年到1925年的这30年,被学者们称之为近代中国的转型期。在转型时代,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不断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随之传入的还有大量新的词汇。英文中的“Society”,就是从晚清开始渐渐出现在国人面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提炼,最后固化为“社会”一词,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用语。那么,中国自身语境中有没有“社会”这个词语呢?“Society”一词传入中国经历了什么过程又带来哪些巨大的变化呢?这本《“社会”的发现》一一给予了回答。
作者首先指出,在中国传统语汇中,“社会”一词早就已经存在。不过,在中国人的语境中,“社”最初是指“土地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又引申为“居住单位”。如《周礼》中就明白无误地记载:当时以25户为一“社”;至于“会”呢,则是指聚集、集会的意思。“社会”二字合用于一体,就是表示节日集会。如《东京梦华录》云:“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春社、重午、重九亦如此。”
所以,今天大家所使用的“社会”,并非中国古代“社会”一词含义的延续,而是来自英文中的“Society”的含义。《牛津字典》对“社会”的解释是:(1)居住在一个或多或少有秩序的共同体中的人的聚集(主要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居住在同一个国家或区域并且拥有共同的习俗、法律和组织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二是指这样一个共同体中的某个特殊部分);(2)一种植物或动物体;(3)一个为特定目的或活动而组成的组织或俱乐部;(4)有他人陪伴的状态。从中可以看到,中西方对于“社会”一词的定义是大相径庭的。
作者梳理发现,早在明代末期,西方传教士就将西方近代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等学问以及建筑、音乐等艺术传入中国。不过,这一时期传入的社会科学著作极少,所以,翻译作品原文中应该很少会用到“Society”这个词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对外开放。于是,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负责对外交涉和洋务事业。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很多官员日渐感觉到了解国际法的重要性。1865年,由清政府拨款资助的崇实馆开始出版《万国公法》译刊,供人们阅读参考。在《万国公法》上,刊登了惠顿的《国际法原理》,“Society”这个词汇随着这篇文章传到了中国。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社会”概念的生成,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被立刻用到实际政治思想活动中。其主要的冲击有:“社会”含义的日趋明晰,反映了晚清精英分子的觉醒,通过翻译、阅读西方文献,不少开明的知识分子从中受到启发,认为中国应该属于人民大众。其次,带来社会伦理观念的革新。作者指出,在“社会”等新词汇输入的同时,西方伦理学学理也慢慢走进了古老的中国。反对“三纲五常”,主张以国家和社会为重的公德观念开始出现。自先秦以来固有的“三纲”“五伦”中的公共伦理,被新的“群己关系”“国家——个人关系”、“社会——个人关系”所取代。
而“社会”的重要性在“五四”前后日益凸显。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感染,“社会主义”风靡全国。在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新青年》所传播的民主主义得到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增大,其所主张的唯物史观也随之越来越受到认可。知识界开始用它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社会;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认为是解决现实问题有效的途径,最终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