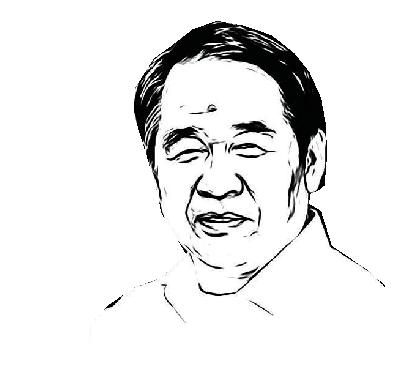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03-06 第27,891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上海城市国际性与中共创立
■ 熊月之
近代上海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国际联系广泛、频繁而深刻。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起于欧洲,进而扩展到北美洲、亚洲、非洲等处,是一种国际性运动。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创立的,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诸多活动带有上海城市特有的国际印记。
近代上海城市的两种国际性
近代上海城市存在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一类是外接式、常见型国际联系,指的是上海与英、法、德、美、俄、日等国家及其城市直接发生的联系。建党时期,上海与欧、美、日各主要港口的定期客轮,已相当便捷,从上海可以直接到达伦敦、马赛、汉堡、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香山、神户等,每条航线都有多家轮船公司经营。由上海通往以上各大城市的电报、电话更是顺畅无碍。
另一类是内嵌式、罕见型国际联系,指的是经与上海租界内各相关国家团体、个人发生的联系,进而延展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近代上海办有多种外文报刊,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均有。这些报刊广泛地报道世界各地信息。上海还设有众多外国通讯社。上海居住着众多外国人。1920年,上海外侨近3万人,来自英、美、法、日、德、俄等50多个国家与地区。这些外侨不光与其母国有诸多联系,还由于经贸、文化、宗教等方面因素,与世界各地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其时,上海存在三个行政管理机构,即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家各自为政,互不统辖。三家之上,没有任何可以统辖或协调三家关系的垂直权力机构。遇到非协调不可的问题,就由各国领事或领事团向上海地方政府交涉,或通过各国驻华公使向中国中央政府交涉。这样,在上海城市内部,华界与两租界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国际关系。中国居民与租界内各国外侨的关系,有时也会上升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
这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有时是单独发生的,如留学生赴美、赴日、赴法、赴俄,直接发生在中国留学生与相关国家之间;有时是交错或合并发生的,如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尼克尔斯基来上海,既有上海与俄罗斯相关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有他们到上海以后利用租界的因素。这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造成了上海城市两种不同的国际性,前者可称为外接式国际性,是正常国际性或一般国际性,这是当时众多涉外城市共有的国际性,如北京、南京;后者可称为内嵌式国际性,是非正常国际性或畸形国际性,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含有多国租界或公共租界的城市才有的。
这两种国际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首先,国际重要事件的发生,每每影响上海城市内部结构,国际一有风吹,上海便会草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大批难民逃出,相当一部分来到了上海,加大了上海与俄国的联系,也改变了上海外侨的结构,使得上海法租界成为俄侨集聚区。共产国际从一开始便看中上海,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很重要原因便是上海有众多俄侨,便于开展工作。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后,上海大批德侨回国,直接影响了上海外侨与外国资本的结构。
其次,上海发生的许多事件,也会酿成国际事件,犹如平静的湖面,上海“一石子”,国际“千重浪”。1905年,上海发生抵制美货运动,不但引起寓沪美国商人的恐惧,也很快成为国际性事件,影响到中美关系,最后在国家层面上才得以解决。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罢课、游行,影响很大,但北洋政府并不十分惧怕。但是,6月5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便影响到英、美、德、法、日等列强在上海的利益,进而影响他们在整个中国的利益,从而造成很大的国际压力,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罢免曹汝霖、陆宗舆与章宗祥的官职。
上海国际性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在这两种国际性综合影响下,上海在马克思主义信息传播、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其活动方面,发挥了远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特殊作用。比如,“马克思”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并述及《共产党宣言》学说的,是1899年在上海出版《万国公报》连载的《大同学》,主译者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众所周知,《万国公报》是教会办的,李提摩太述及马克思与《共产党宣言》,本是作为一种新的学说介绍的。但是,从传播学角度看,则是由一个具有跨文化身份的传播主体(李提摩太),通过新式媒介(《万国公报》),将一种新的知识从这种知识的生产地欧洲传到了中国,从而完成了这种新知识的国际传播。自1920年8月至1922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读物18种,包括《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俄国共产党党纲》《列宁传》《李卜克内西纪念》等,全部在上海出版。上海能够获得这么多新的知识,全赖于其广泛的国际性。
共产国际垂青上海
共产国际自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之日起,就在努力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并将目光投向了上海。1920年4月,负有指导筹建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一行来到上海。随后,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建立(今虹口长治路177号),中俄通信社、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九江路14号)等机构设立。苏俄、共产国际向其驻华代表、在华机构,以及中共组织及其他革命组织提供的经费,相当一部分便是通过这个办事处支付的。
就空间距离而言,从俄国西伯利亚到上海,比起到北京、天津要远得多,北京还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但共产国际不是将此机构设在北京、天津,也不是设在另一个东亚大城市东京,而是设在上海。这与上海城市高度的国际性有直接关系。共产国际成立的1919年,上海已是拥有245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最大的港口城市、最为开放的城市,是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城市。这些,都是共产国际特别看重的地方。
这些机构,以上海为基地,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作为经费周转站,以《上海俄文生活报》为信息载体,还有日夜不息的电波,将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信息传递到上海,扩散到全中国,又将中国的信息传递到苏俄,在中国与共产国际、苏俄之间架起了信息通道。那么多外国人,不时地来往于上海与北京、上海与哈尔滨、上海与广州等地,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建党初期起了相当重要作用。显然,没有上海这一独特的城市,这一切都难以想象。
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1920年得以成立;中共一大在1921年得以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中共一大举行期间,有巡捕闯入、查问,迫使会议转移地方,也与上海城市的国际性直接有关。学术界研究已经表明,巡捕是冲着马林来的。马林早已引起欧洲反共势力的关注,他离开欧洲以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到了上海,他一直是工部局重点关注的对象。
与上海高度国际化相一致,民国时期上海金融高度国际化,美元等各种外币在这里都可以便利地汇兑为中国通用货币。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都有效地利用这一特点。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近代上海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国际联系广泛、频繁而深刻。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起于欧洲,进而扩展到北美洲、亚洲、非洲等处,是一种国际性运动。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创立的,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诸多活动带有上海城市特有的国际印记。
近代上海城市的两种国际性
近代上海城市存在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一类是外接式、常见型国际联系,指的是上海与英、法、德、美、俄、日等国家及其城市直接发生的联系。建党时期,上海与欧、美、日各主要港口的定期客轮,已相当便捷,从上海可以直接到达伦敦、马赛、汉堡、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香山、神户等,每条航线都有多家轮船公司经营。由上海通往以上各大城市的电报、电话更是顺畅无碍。
另一类是内嵌式、罕见型国际联系,指的是经与上海租界内各相关国家团体、个人发生的联系,进而延展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近代上海办有多种外文报刊,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均有。这些报刊广泛地报道世界各地信息。上海还设有众多外国通讯社。上海居住着众多外国人。1920年,上海外侨近3万人,来自英、美、法、日、德、俄等50多个国家与地区。这些外侨不光与其母国有诸多联系,还由于经贸、文化、宗教等方面因素,与世界各地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其时,上海存在三个行政管理机构,即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家各自为政,互不统辖。三家之上,没有任何可以统辖或协调三家关系的垂直权力机构。遇到非协调不可的问题,就由各国领事或领事团向上海地方政府交涉,或通过各国驻华公使向中国中央政府交涉。这样,在上海城市内部,华界与两租界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国际关系。中国居民与租界内各国外侨的关系,有时也会上升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
这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有时是单独发生的,如留学生赴美、赴日、赴法、赴俄,直接发生在中国留学生与相关国家之间;有时是交错或合并发生的,如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尼克尔斯基来上海,既有上海与俄罗斯相关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有他们到上海以后利用租界的因素。这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造成了上海城市两种不同的国际性,前者可称为外接式国际性,是正常国际性或一般国际性,这是当时众多涉外城市共有的国际性,如北京、南京;后者可称为内嵌式国际性,是非正常国际性或畸形国际性,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含有多国租界或公共租界的城市才有的。
这两种国际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首先,国际重要事件的发生,每每影响上海城市内部结构,国际一有风吹,上海便会草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大批难民逃出,相当一部分来到了上海,加大了上海与俄国的联系,也改变了上海外侨的结构,使得上海法租界成为俄侨集聚区。共产国际从一开始便看中上海,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很重要原因便是上海有众多俄侨,便于开展工作。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后,上海大批德侨回国,直接影响了上海外侨与外国资本的结构。
其次,上海发生的许多事件,也会酿成国际事件,犹如平静的湖面,上海“一石子”,国际“千重浪”。1905年,上海发生抵制美货运动,不但引起寓沪美国商人的恐惧,也很快成为国际性事件,影响到中美关系,最后在国家层面上才得以解决。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罢课、游行,影响很大,但北洋政府并不十分惧怕。但是,6月5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便影响到英、美、德、法、日等列强在上海的利益,进而影响他们在整个中国的利益,从而造成很大的国际压力,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罢免曹汝霖、陆宗舆与章宗祥的官职。
上海国际性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在这两种国际性综合影响下,上海在马克思主义信息传播、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其活动方面,发挥了远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特殊作用。比如,“马克思”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并述及《共产党宣言》学说的,是1899年在上海出版《万国公报》连载的《大同学》,主译者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众所周知,《万国公报》是教会办的,李提摩太述及马克思与《共产党宣言》,本是作为一种新的学说介绍的。但是,从传播学角度看,则是由一个具有跨文化身份的传播主体(李提摩太),通过新式媒介(《万国公报》),将一种新的知识从这种知识的生产地欧洲传到了中国,从而完成了这种新知识的国际传播。自1920年8月至1922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读物18种,包括《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俄国共产党党纲》《列宁传》《李卜克内西纪念》等,全部在上海出版。上海能够获得这么多新的知识,全赖于其广泛的国际性。
共产国际垂青上海
共产国际自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之日起,就在努力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并将目光投向了上海。1920年4月,负有指导筹建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一行来到上海。随后,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建立(今虹口长治路177号),中俄通信社、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九江路14号)等机构设立。苏俄、共产国际向其驻华代表、在华机构,以及中共组织及其他革命组织提供的经费,相当一部分便是通过这个办事处支付的。
就空间距离而言,从俄国西伯利亚到上海,比起到北京、天津要远得多,北京还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但共产国际不是将此机构设在北京、天津,也不是设在另一个东亚大城市东京,而是设在上海。这与上海城市高度的国际性有直接关系。共产国际成立的1919年,上海已是拥有245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最大的港口城市、最为开放的城市,是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城市。这些,都是共产国际特别看重的地方。
这些机构,以上海为基地,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作为经费周转站,以《上海俄文生活报》为信息载体,还有日夜不息的电波,将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信息传递到上海,扩散到全中国,又将中国的信息传递到苏俄,在中国与共产国际、苏俄之间架起了信息通道。那么多外国人,不时地来往于上海与北京、上海与哈尔滨、上海与广州等地,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建党初期起了相当重要作用。显然,没有上海这一独特的城市,这一切都难以想象。
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1920年得以成立;中共一大在1921年得以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中共一大举行期间,有巡捕闯入、查问,迫使会议转移地方,也与上海城市的国际性直接有关。学术界研究已经表明,巡捕是冲着马林来的。马林早已引起欧洲反共势力的关注,他离开欧洲以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到了上海,他一直是工部局重点关注的对象。
与上海高度国际化相一致,民国时期上海金融高度国际化,美元等各种外币在这里都可以便利地汇兑为中国通用货币。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都有效地利用这一特点。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