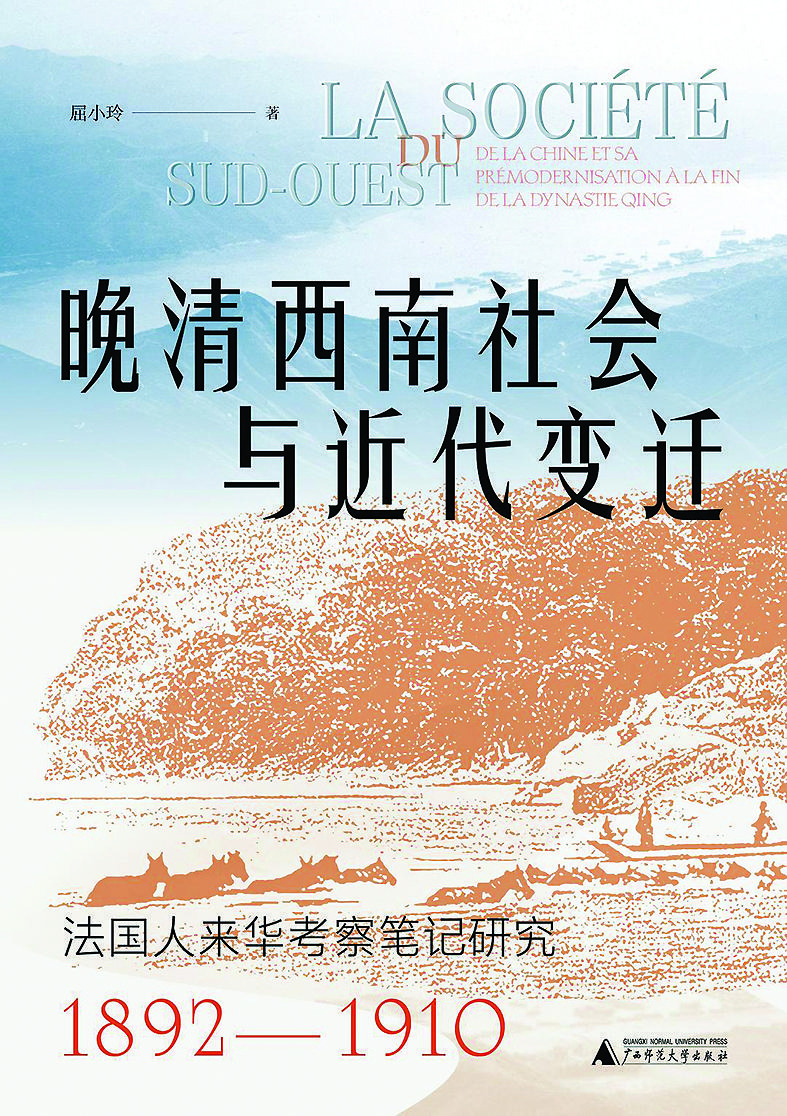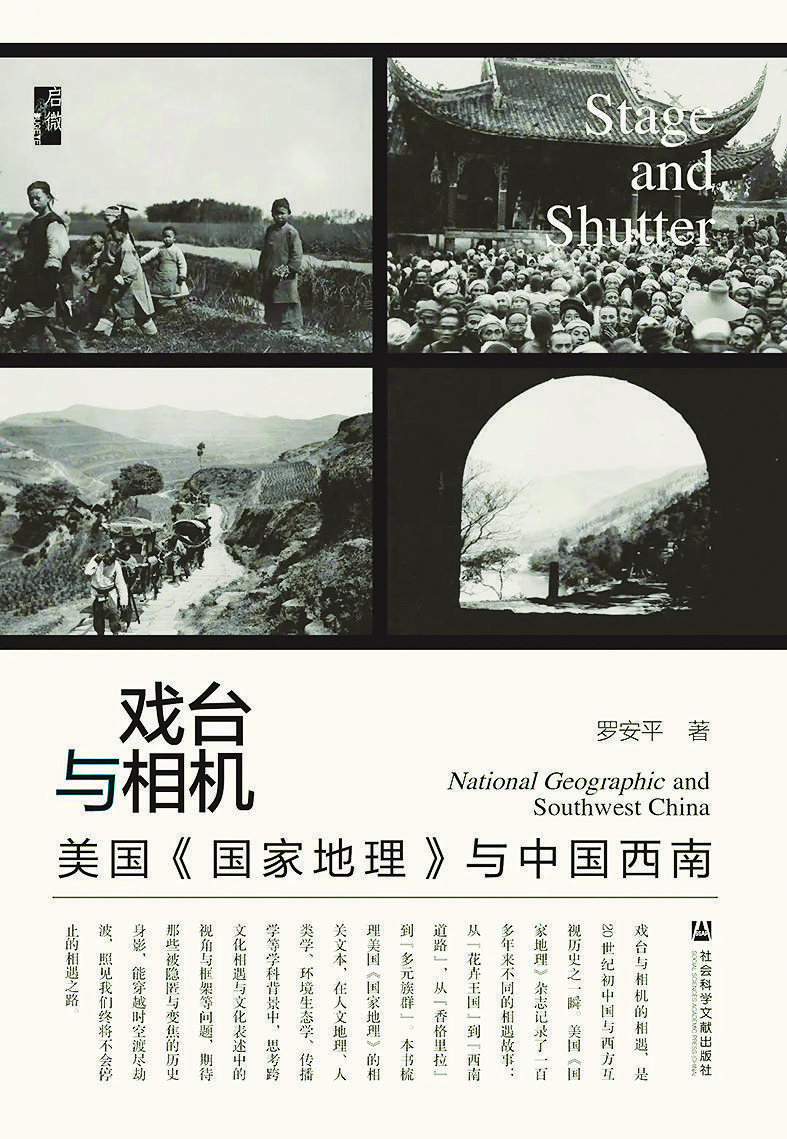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3-12-03 第27,797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记录大西南:从“异域奇观”到“本土影像”
《晚清西南社会与近代变迁:法国人来华考察笔记研究(1892-1910)》 屈小玲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池骋对于像我这样长期生活在平原的人来说,大西南因其山峦层叠而显得遥远神秘。直至近日,连续阅读了三本和西南有关的著作,对这片区域的印象才变得丰满起来。这三本书,屈小玲的《晚清西南社会与近代变迁:法国人来华考察笔记研究(1892-1910)》、罗安平的《戏台与相机:美国〈国家地理〉与中 国西 南》,以 及马 晓峰、庄钧主编的《庄学本:西行影纪(1934-1941)》,尽管论述对象各异,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却奇妙地串连为思想上的连贯性和认知上的共同性,让读者更真切地触摸到中国的西南。
差异与神秘:与“中原”相对的“西南”
自从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就作为一个与“中原”相对的地理和文化空间被纳入主流叙事。历经两千多年,“西南”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内涵发生了诸多变化,可有意思的是,其差异性和神秘性不仅没有被主流叙事消解,反而不断增长,渗透到大众的认知之中。就拿《鬼吹灯》系列来说吧,这套本世纪初火遍大江南北的网络小说,竟有四部将故事背景设定在西南地区。这说明,在大众文化中,“西南”已然成为一种制造悬疑氛围的符号。只要这个符号出现,受众的肾上腺素就会自动分泌。
这和西南的独特区位有关。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包括云南、四川、贵州,这构成了狭义上的西南。如果加入西藏和广西,算上湘西、鄂西,则是广义上的西南。这片广袤区域恰好位于著名的“胡焕庸线”以西。胡焕庸线又名“瑷珲—腾冲线”,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画一条线,其东侧地貌以平原、水网、丘陵为主,适宜农耕,分布着我国96%的人口;西侧多为山地、草原、沙漠、雪域,人烟稀少,只分布着我国人口的4%。东西两侧的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
胡焕庸线揭示了我国人口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格局的分界,也凸显出西南地区的特质——无论是自然地貌、气候生态,还是生活方式、人文环境,它都和胡焕庸线以东,即通常说的中原地区迥然有别。这种异质性使其自带神秘光环。更重要的是,胡焕庸线的存在或许是西南的历史记忆未被主流叙事消解的主因。要知道在古代的物质条件下,地理障碍是很难抹平的。也正因此,当西方人初入西南,会产生来到“另一个中国”的观感。
我们知道,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执行“一口通商”政策以来,西洋商人只能在广州一隅活动。对此,洋商是不甘心的,千方百计突破禁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条约,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洋商终于得偿所愿。他们遂以这些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口岸为据点,不断拓展,很快将整个东南地区编织进全球性的商贸网络。然而,向西南探索却遇到了诸多不顺。一是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进入西南,殊为不便;二是清政府不希望西方人把手伸得太长,为此设置重重阻碍,致使其步履迟缓。
至19世纪末,情况悄然改变。当时,英法等加快殖民东南亚的步伐。英国完成了对缅甸的全面殖民,法国完成了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殖民。东南亚与云南、广西接壤,西方人便借由这一通道前往西南。西方人的到来,让西南跳脱出传统主流叙事的单一滤镜,得到了外部视角的观照。
初来者:法国人的商务考察
西方人探访西南的首要动机是开拓市场,获取商业利益,用罗安平教授的话说就是试图“将西南乃至中国纳入东方殖民市场体系”。
这在法国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屈小玲的研究表明,为了给国内的工业品打开销路,法国政府急欲开拓海外市场,中国西南被锁定为重要目标。从19世纪末开始,法国人多次组织考察团深入西南调研。在《晚清西南社会与近代变迁:法国人来华考察笔记研究(1892—1910)》一书中,屈小玲梳理相关史料,生动再现了这些考察团的历程。
首先,它们有着明确的商务目的,甚至能细致到某一细分领域。比如里昂商会考察团,由里昂商会牵头,联合马赛、波尔多等六座法国城市的商会组成。这些城市均以纺织品闻名,里昂更是号称“欧洲丝绸之都”,这决定了该考察团最关注纺织业,其成员亦多为纺织专家。里昂商会考察团历时近两年,足迹遍布西南各地,摸清了当地纺织业及轻工业的基本情况。
随着越来越多的法国考察团涌入,西南地区的农业形态、水陆交通、公益事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揭示。在这个过程中,考察团不可避免地会与当地人发生接触,交流互动也日益频繁。凡此种种都载入了考察笔记。
值得一提的是,考察团里往往有一两位具备学术背景的成员,他们为考察增添了社科研究的色彩。商务考察团怎么会带学者呢?这其实是西方在近代殖民活动中生成的一种传统——凡是踏入异域,都要搜集材料,以便掌握当地的历史和文化。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就带了包括考古学家、博物学家在内的175位学者,收集雕塑、石碑、莎草纸,构成了埃及学的基础。可见,殖民从不止步于经济,而会向思想殖民、文化殖民延展。
当然,法国考察团距此尚远。他们的重心落在商务,对风土人情的描摹,也是为了把握当地的商业环境及商业逻辑。不过这也很珍贵。由于来自异域,在“外部视角”的观照下,西南的山水、桥梁、寺庙、教堂、街市,以及在其间活动的马帮、背夫、各族居民,都显现出别样的色彩。特别是他们对日常民生的观察和记录,是中国传统叙事中少见的。
这些外来者还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变迁在微观层面的影响。在昆明,考察团拜访了一个名叫王炽的商人。王炽出身贫寒,因抓住机遇,通过出口贸易而跻身当地首富,实现了阶层跃迁。1901年清政府施行所谓“新政”,四川各地出现了女子放足、兴办女学的盛况,也为考察团注意并记录。他们看重的是潜在的女性市场,却也勾勒出一个老大帝国在内外冲击下的变化。
新视野:大西南的人类学价值
法国考察团毕竟以商业为要务,囿于视野,难免排除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相形之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西南的探索就全面、深入得多。这和《国家地理》的办刊宗旨密不可分。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罗安平在《戏台与相机:美国〈国家地理〉与中国西南》一书中就此做了阐释。
《国家地理》为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官方刊物,1888年创刊,致力于向大众传播通俗化的地理知识,同时“运用大量摄人心魄的图片与形象描述,清晰、准确而生动地反映这个激动人心的世界及其生命”。在撰稿人和摄影师的选择上,《国家地理》非常强调他们的人类学资质。这意味着,撰稿人和摄影师不仅仅是浮光掠影的看客,还应该像人类学家那样进行田野调查。由此,《国家地理》形成了一种将“地理知识、旅行游记、文学作品与民族志”相融合的独特风格,罗安平称之为“人类学写作”。
强烈的人类学取向促使《国家地理》将目光投向中国西南。这是必然的,因为西南在人类学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第一,近代以来西南是东西方文明相遇与交汇的重要场域,双方激荡出怎样的化学反应,值得探究;第二,西南本身是多元文化碰撞地,汇聚着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25个,族群多样性带来的语言、宗教、习俗多样性,是人类学的中心课题;第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又使西南成为生态热点地区,吸引人类学家前往。
据统计,创刊至今130多年,《国家地理》刊载与中国相关的文章300余篇,直接书写西南的40多篇,居中国各区域之首。这份杂志对西南的偏爱可见一斑。罗安平的《戏台与相机》从植物采集、西南道路、生态文明、族群形象四个维度,解析了《国家地理》这长达130多年的西南之旅。
解构“凝视”:庄学本的再书写
如何评价《国家地理》与中国西南的关系?罗安平认为,应该承认,它极大地增进了英语世界对中国西南的认知。约瑟夫·洛克笔下的纳西族巫师、谭恩美对侗寨与侗族大歌的介绍,既是人类学经典,更是让英语世界认识这些民族瑰宝的“爆款”,对跨文化沟通与对话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除此之外,我认为还可补充一点。如前所述,司马迁时代西南已被纳入我国的主流叙事。不过,在这种叙事套路中,西南从未获得过和中原相对等的地位,相反,作为被规训对象,其主体性是欠缺的,丰富性也被减损。而人类学遵循的“客观中立”学术准则,则给予西南更强的主体性,并将其丰富性做了原生态呈现。这可以视作现代知识对传统叙事的某种矫治。
当然,对此也不能估计过高。诚如罗安平指出的,即便力图保持客观,《国家地理》也难免带着优越感去看待它记录的对象。实际上,这也是20世纪初人类学的通病。当时的人类学家热衷于探访前现代社会,甚至认为这才有研究价值——其实质,是“文明”的西方凝视“野蛮”的东方。于是我们看到,《国家地理》的镜头和文字往往带有猎奇色彩,似乎意在展示某种“异域奇观”,与法国考察团对照,反倒缺少了平凡的日常景象。
显然,西方中心论的偏颇还需东方人来纠正。这就要提到一位传奇人物——纪实摄影大师、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庄学本。
庄学本,1909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家贫,幼年辍学,辗转沪上做练习生和小职员,期间掌握了摄影技术。1930年,庄学本和几位知识青年相约组成全国步行团,从上海到北平,一路进行社会调查、图片拍摄、证物搜集。此次壮游点燃了庄学本的热情,他立志以“徒步考察+影像记录”的方式遍览祖国,振奋民族精神。首选即为西南。从1934年到1941年,庄学本行走于西南各地,用照相机拍摄鲜为人知的边地风俗与人物,还绘制地图,搜集标本,记录口述传说,留下了万余张照片及上百万字的一手资料。
马晓峰、庄钧主编的《庄学本:西行影纪(1934-1941)》,精选庄学本摄影代表作,也详细展现了他一生的行止。阅读这套书,能明确察觉到庄学本的与众不同。和传统中国的主流叙事相比,他没有中原王朝俯瞰“化外之地”的傲慢;和西方观察者相比,他有着基于国族认同的共情,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西方人的“凝视”。
总之,庄学本的镜头是平视而深邃的,文字是具有包容性和理解力的。观看这一张张照片,细读这一篇篇笔记,是一趟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朱靖江在为本书做的长篇导论中,精准描述了我的这种阅读感受。他写到,庄学本的影像将“一种文明与尊严的力量赋予了他所观照的边地人民”,因而无论康巴青年还是嘉绒少女,果洛活佛还是藏地贵族,都能超越时空的疆界,透过照片的边际,“与我们目光交汇,情感相通”。
如果以1892年第一支法国考察团进入西南为起笔,以庄学本1941年在重庆等地举办影展为落笔,时光的步履正好走过半个世纪,而西南也完成了从“异域奇观”到“本土影像”的转换。自那时起,西南得到了新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