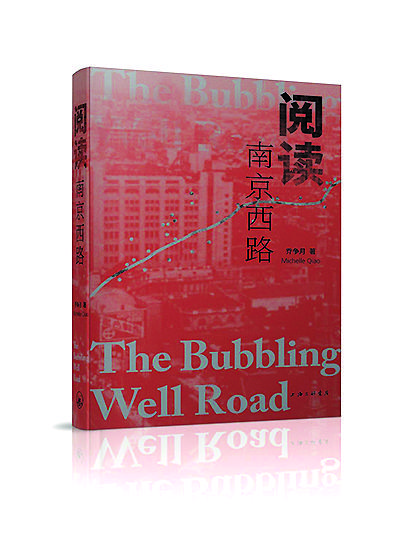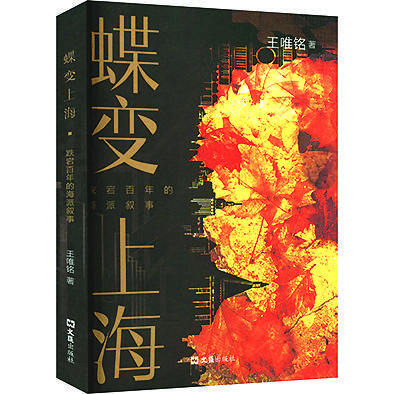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3-04-02 第27,552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从我们的“附近”出发,走向历史深处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项飙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池骋如果说人类学家项飙关于“附近”的论述和提倡,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眼界(他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即是对此观点的集中展示),那么,郑亚的《海上华痕——一个人的博物叙事》、乔争月的《阅读南京西路》和王唯铭的《蝶变上海:跌宕百年的海派叙事》,则是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呈现了了解“附近”的可能性,以及“附近”的无限延展性。
关注“自己的附近”
一位热爱植物的朋友曾经问我:你知道上海有多少种植物吗?哪些属于乡土植物,哪些又是外来的?我一时茫然。彼时我们正从福州路往上海博物馆走,他一路指点,不长的路程中竟然数出了十多种植物,并一一讲述它们的渊源与特性。我大受震撼,同时为自己对周遭事物的无知而感到愧疚。我也想起多年前去浙江衢州采访簾师程宵春的经历。“打纸簾”是宣纸制作的重要环节,出身簾师世家的程宵春当然深通此道,真正令我惊讶的,是他对本乡本土的熟稔:举凡鸟树鱼虫,无不如数家珍,堪称一位博物学家。而且并非程宵春如此,他的乡亲皆如此。和他们比,我纯属孤陋寡闻。
我的困惑在于,程宵春安居的乡土拥有丰富的自然景物和农耕景观,人们浸淫其间,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关于周遭的知识体系;而我生活于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似乎缺乏这样的条件。但那位植物迷朋友给了我启迪——街道两旁的香樟、悬铃木,小区里的黄鼠狼、刺猬,还有野趣盎然的远郊,其实只要用心身边,我也能收获大量乡土知识。
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人类学家项飙的观点进一步拓宽了我的视野。在和非虚构作家吴琦的对谈中,项飙反复提及要观察“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努力用“自己的语言”把它叙述清楚(见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项飙的代表作《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上世纪80年代,一群以浙江温州人为主体的商贩聚居到北京南苑地区,形成了“浙江村”。当时还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的项飙,利用同乡之便浸泡六年,以琐碎的方式记录浙江村日常,逐渐勾勒出这个小世界的各个面相。值得注意的是,《跨越边界的社区》语言平实,很少学术术语,贯彻了项飙“把事情说清楚”的原则。
近两年,项飙把带有学术色彩的“小世界”一词置换成通俗易懂的“附近”,表述也越来越直观。他鼓励每个人注意观察附近的人、事、物,探究它们的历史渊源、相互关联和运行逻辑,建立起有关于“附近”的知识。借助这些知识,人就能够搭建自身和周遭事物的稳定关系。
我认为这一点之于城市人无比重要。像上海这种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超大型都市,哪怕你生于斯长于斯,都难以在如此巨大的尺度上建立起认同感。因为大尺度空泛、不亲近,而人对某地的认同感,往往是以自身所活动的物理空间(即附近)为圆点向外扩散的。没有对“附近”的认知和体会,人就很容易被打散成原子状态,成为飘荡于数字平台的无根游民。
从这个角度讲,了解“附近”既是建立城市认同感的起点,也是树立生活信念,追寻我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起点。“附近”的意义由此凸显。
从“附近”出发的资深文博人
郑亚新著《海上华痕——一个人的博物叙事》就是一本探索“附近”的好书。全书分为“观博寻踪”和“读城阅市”两编,前者恰好是郑亚工作的“附近”,后者则从“附近”延伸出去,对城市进行“考古”。
郑亚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文物与博物馆专业,长期在上海文博系统工作,现为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因此,与文博有关的人、事、物,都能构成她的“附近”。
在“观博寻踪”编中,郑亚从复旦文博系小楼讲起。郑亚的忆述是细致而温情的。在底楼南侧的大教室里,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青铜器研究大家陈佩芬给他们上课,不苟言笑的陈先生将种类繁多的青铜器讲得一清二楚。她的口头禅是:“青铜器不要太有劲哦!”底楼北侧的实验室则是上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课的地方,郑亚在文中写道,她曾上手过一件“拦腰断裂的兵马俑”和一尊“身首分离的唐三彩”,饶有趣味。楼下的小花园也是郑亚乐于盘桓的所在,从字里行间中能看出,那婆娑的树枝、池塘里的倒影,至今令她魂牵梦绕。
从复旦200号文博系小楼出发,作为“文博人”的郑亚追溯了自己与上海诸多博物馆的交集,其中既有上海博物馆、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大咖”,亦不乏大学博物馆、女性主题博物馆等小而美的场所。而前往博物馆途中的名人故居,如大陆新村鲁迅故居、长乐邨丰子恺旧居、武康路巴金故居等,更是勾连出一条可供徒步的文旅线路。
进入“读城阅市”编,随着郑亚的触角不断延伸,她的“附近”由线扩成了面,申报馆、泥城桥、永平里、张园、豫园、人民公园……皆纳入视野。而郑亚的描述绝不仅仅停留于外部,而是带有浓郁的私人感情。例如,少女时代郑亚曾在永安公司购得一条漂亮的裙子,从那时起永安就成了她心目中的样板,往后数十年她只在这样的商铺里挑选服饰。
经年累月的走读,让郑亚记录下“附近”的演变。十多年前逛茂名路,她与沿街小店的阿姐讲闲话,在弄堂口围观洋新郎迎娶上海女孩,去小餐馆吃辣酱面……此情此景已难再现,我们只能通过郑亚的记录追忆这份温情。
受郑亚启发,我也根据工作半径,有意识地探索自己的“附近”。这一转有了新发现。原来我一直擦身而过的武定西路1375号,早先叫开纳公寓,开纳公寓不远处的愚园路江苏路口竖着一块名人故居指示图,新感觉派作家、文史学者施蛰存故居就在背后的弄堂里。从1938年搬入到2003年逝世,他在这里住了65年。谁能想到,享誉学界的“北山楼”竟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这次收获激起了我进一步的兴趣,我开始关注更多与“附近”有关的书籍。《阅读南京西路》是又一本适合边走边读的书。书不厚,作者乔争月的讲述却很细致,将33幢南西建筑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我以为本书最独到之处,是频繁征引老上海的英文报刊,如《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大陆报》等。这些珍贵的史料,一下子将老建筑拉回到当年的社会场域,赋予其鲜活的现场感。乔争月此前与人合著的《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也都是不错的“走读指南”。
走向历史深处的城市狩猎者
在“附近”兜兜转转的这段日子,让我又一次体认到上海这座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所蕴含的现代性特征。例如,无论鲁迅与施蛰存、茅盾、邵洵美、庐隐之间存在多少差异,他们都用白话文写作,都栖居于弄堂,也都按照都市的节奏作息。他们事实上都被编织进了现代生活的网络,共享某些空间和知识。而如今,我也身处这张网络之中,这使我和他们具有了某种亲缘性,进而产生了深入了解的兴趣。换言之,我从“附近”出发,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区域,也走向了历史深处。
此时,案头的这本《蝶变上海:跌宕百年的海派叙事》就显现出了价值。作者王唯铭,常年游走大街小巷,有“城市狩猎者”之称。20多年来,这位狩猎者出版了多部与上海有关的著作,尤其近几年,他的足迹以“附近”为原点越走越远,且表现出清晰的寻根意识。从2015年的《苏州河,黎明来敲门》到2017年《十个人的上海前夜》,再到最新的《蝶变上海》,王唯铭“全景式叙说”海派文化的雄心展露无疑。
在《蝶变上海》中,作者将海派文化分为上海意识、现代器物、生活方式三个层面,并逐次解析。所谓上海意识,指上海人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从对峙到和解再到融合,形成了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海派底色。如果说上海意识尚属于抽象范畴,那么现代器物就十分具象了,举凡电灯、自来水、照相馆、抽水马桶、汽车、电话、电影……正是这些新事物,让海派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是海派文化依托的土壤。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上海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如穿皮鞋、吃西餐、看电影、跳交际舞等等。
作者特别提及,1890年代至1910年代,上海出现了一个人数大约在50万的新阶层(俗称市民阶层),包括技术工人、小商贩、小业主、洋行职员、媒体记者、自由撰稿人等。他们是海派生活方式的核心人群,是现代器具的使用者和推广者,也是上海意识的承载者与传扬者。
如今,走在淮海中路、南京西路,走进焕新回归的张园,徜徉于作者用巴洛克式语言描绘的“十里洋场”,我仿佛能看到那些100多年前的身影。他们穿越纸墨,从历史深处款款而来。就这样,借助这些书籍,往昔与当下交织,我的“附近”也日益丰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