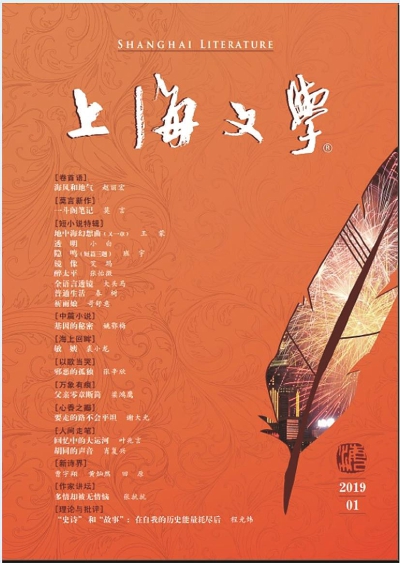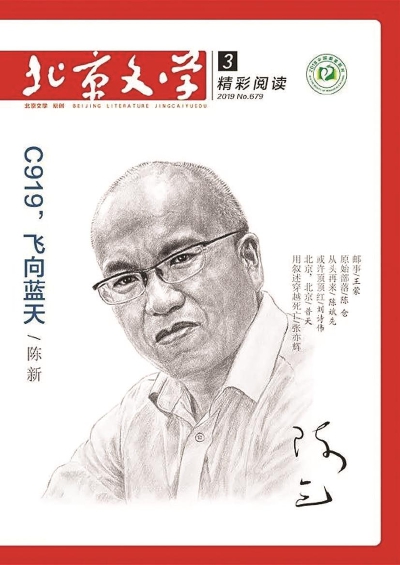■嘉宾:王蒙(著名作家) ■采访:许旸(本报记者)
【本报独家对话】
85岁作家王蒙,笑称自己是“耄耋腹肌男”,常年坚持游泳、快走,过去几年微信步数日均九千步,笑傲朋友圈。亲朋好友担心他的膝盖受损,“如今我把标准降到每天七千步左右了”。
步数少了,但创作依然高产。今年以来,《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纯文学刊物上分别发表了他的中短篇小说《生死恋》 《地中海幻想曲》 《邮事》,他还和两位学者合著出了两本书分别谈睡眠与传统文化,超50卷的《王蒙文集》预计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王蒙有自己的“任性”与笃定,任性在于,他在新写的中短篇里试图给小说种种既定技巧“松绑”,乐此不疲地拆除形式的篱笆,“散养”自己的小说。但他也明白适可而止,正如王蒙所说——再充实忙碌,也得把握节奏,把握心态,只能耄耋,不能饕餮,乐天知命。
生活处处有余音,文学恰是对过往的命名与沉淀
文汇报:您最新发表的中篇小说《邮事》讲述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鸿雁传书”,穿草绿色职业装、骑着自行车、斜挎敞口帆布袋的邮递员意象十分鲜活,接近于“回忆录”式写作。您把《邮事》定义为“非虚构小说”,这个文体概念很新。小说向来以“虚构”见长,为何把“非虚构”与“小说”嫁接?
王蒙:有研究报告文学的朋友不接受“非虚构小说”这一说法,但我这篇作品又决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邮事》就是要充分发掘对于非虚构的人与事的小说化可能,使非虚构的一切生活化、故事化、趣味化与细节化。
时代日新月异,生活飞速前进,如今人们很少手写寄信了。手机通话、语音、视频十分方便,大量新事物涌现,通信方式的变迁折射中国巨变。但就在几十年前,许多美好都是通过邮政传布的,“邮政邮件,比火车更能奔跑与拓新,不声不响,它们永远是激流,是风驰电掣,是与时间赛跑……”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往事不时浮出水面。我记叙生活的变化,定格日常瞬间,有怀旧,有欢呼,有新鲜感,有沧桑感。
出于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把生活中每份职业、人与人关系中值得留恋珍惜的部分,赶紧记录下来。我们每天都迎接新变化,同时与过去的东西告别,但不是告别了就结束了,任何事物不是天生如此,生活处处有余音。写下来,就体现出文学恰到好处的“细心”与“沉淀”。
全世界都用逝水象征时间,而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有所命名与纪念,这就是文学。文学激活了回忆、过往、昔日、历史;文学是对时光的挽留、对记忆的珍惜、对日子的储存。文学是人类的复活节日——复活,更加确认了也战胜了失去,使得没有对应办法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生成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动。
文汇报:这种“以实对虚”的笔法,在您上一部中篇《女神》中,已觅得踪迹——由现在时牵动过去时,飘逸的、关联或不关联的意象,如彼此追赶的舞伴,翩翩生姿。有评论认为,《女神》有意剥除了情节严格的因果逻辑,打碎线性时间,在史实中掺入梦境,将个体史拼贴成了波普艺术。您怎么看?
王蒙: 《女神》中,我以 “王某”“王蒙”的第一人称直接上阵,其间穿插了自己在新疆、瑞士日内瓦、北京等多地的生活瞬间。这些真实素材星罗棋布地嵌入小说,对人生的感悟与文学理念则游走于意识流情节里,就像做了绵延几十年的梦。“女神”陈布文有真实原型,艺术家张仃的夫人,年长我十几岁,曾写小说,擅京剧,一生高洁。我没见过陈大姐本人,与她仅一信之缘,零散读了她的作品、她与子女亲朋的通信,其才华、修养、品格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于是,便琢磨出了这虚实交错、真实与想象交织的写法。
小说里,想象也可以有所区分,非虚构的想象,货真价实的想象,与虚构的、作态的想象,前者当然比后者感人。说到底,文学填补了人生的某些失落与失意,使一切俗人们认为是白干了白费了白过了的经历得到纪念与反刍,使一切的蹉跎与遗憾变成智慧与心得,使沃土与非沃土上都长成了奇葩……
一切方法、流派、对风格的追求都为我所用
文汇报:中短篇小说一直是您尝试叙事艺术创新的“试验田”,青年批评家贾想有个比喻——“《生死恋》不是流水线上供给市场的热销品,是王蒙建造给自己的舞池、游乐园和希腊小庙。小说在此还原为心灵的游戏,还原为无目的性的审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尝试将各种流派强行给小说的既定范式“松绑”?
王蒙:我试着用一种反小说的方法来写,人们一般认为小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物、故事、环境,有时再加上时间、地点,但我偏偏不这样写。我把内心里最深处的那些情感、记忆、印象、感受堆积成反应堆,并点燃。
我一贯主张的是:我对任何写作的手法或方法都不承担义务。也就是说,一切方法、一切流派、一切对风格的追求都为我所用。我并不是为了创造一种风格而写作,而是用什么风格或手法能更好地表达,追求一种与众不同。至于意义,有一般的意义,典型的意义,也有有待发现的意义,给人以陌生感的意义。
文汇报: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您提出 “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话题。眼下“纯文学的黄金期已过”“小说不占据C位了”等声音此起彼伏;一些经典文学也被冷落或简单标签化。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王蒙:随着新媒体发展,信息的碎片化、视听艺术崛起,文学阅读的确受到冲击甚至冷落,人们逐渐不满足于只有文字的世界。但文学的力量和重要性无可取代,是所有文艺样式中的“硬通货”。影视剧、舞台剧、音乐剧等都需要文学的脚本和源头,所有的欣赏与理解,都需要文字的解说至少是传达。
毕竟,语言文字是人类思维的符号与依托,使想象力、逻辑思辨能力、记忆力、表述与传授能力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耳目也激发驱动思维,但思维离不开语言的符号,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思维的艺术,是头脑与心灵智慧上的极致,而不仅仅是感官刺激。
如今传播环境有个趋势,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褶。不大读书的人、人云亦云的人,成为段子手,这不仅表现在当代人际交往里,也会向着古今中外的经典发射,“喷子式吐槽”多过理性批评。随着书香中国的发展,情况会越来越好的。
在还没到“明年”的时候,我仍然朝气蓬勃
文汇报:2019开年时您吐露“恰恰是今年,感觉到自己开始衰老,听力、视力、牙口、安排日程能力,都在下行”。您觉得自己在创作上是更“随心所欲”了,还是也存在“写作焦虑”?
王蒙:我加入中国共产党71年了,写小说66年了。曾孙过了一岁生日,今年在杂志上接连发了好几个中短篇,合著出了两本书。但这也没啥骄傲的,你想老友徐怀中90岁了还写出新长篇《牵风记》,比我小8岁的冯骥才大个子出了长篇新作《单筒望远镜》。我那骄傲自满的情绪被压得结结实实,我会以徐怀中为榜样,继续收起尾巴,只要还活着,希望也写到90岁。
2019年肯定是充实忙碌的,当然也得把握节奏和心态,只能耄耋,不能饕餮。不管状态怎样,写起小说来,每一粒细胞都会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近几年,我还喜欢用一个说法——“明年我将衰老”,在还没到“明年”的时候,我仍然朝气蓬勃。
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对于传统文化的阅读与评析,也在如火如荼进行。我只能用干活出活来迎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