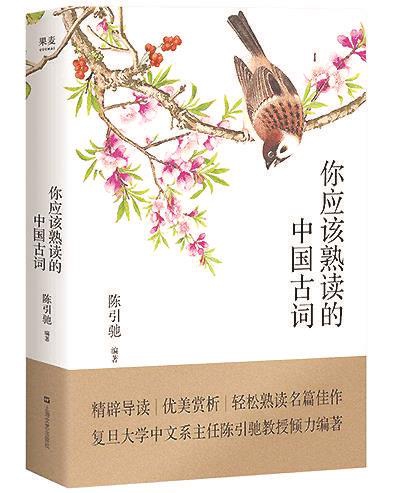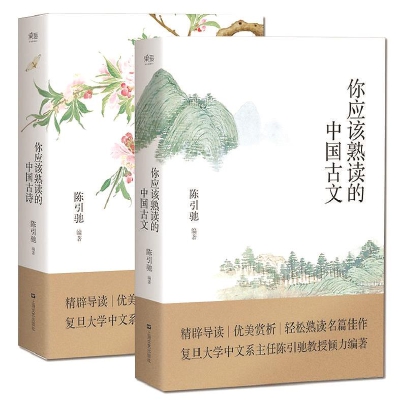本报记者 刘力源
“我们希望做成这样一本书,可以置于孩子的床头,放在客厅的茶几上,装进旅行途中的背包里,可以在春日的午后,写作业的间隙,通勤的公车和地铁里,翻开来读几页,一整天都会感到生动明亮。”陈引驰在他编著的《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诗》导言中这么写道,这段话也出现在同系列的古文、古词选本中。
令一整天“生动明亮”的,一定是那些文辞优美、感发人心的作品。之后,孩子和初学者们才可能去亲近和理解黄钟大吕与泣血哀歌。陈引驰希望,这“第一次看海”留下的美好印象,能够内化为现代中国人最基本的传统素养和文化认同。
近日,《文汇学人》采访了陈引驰教授,请他谈谈什么样的古诗、古文与古词最适宜接通进孩子与大众读者的现实生活,又应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普及过程中的争讼种种。
提供一个不下海的观澜平台
文汇报:您编著这套书的初衷是什么,尤其是古文?
陈引驰:时下各种古典文学的诗选、文选确实非常多,但是各自的类型、功能和所设想的读者对象是很不一样的。这套书主要是想针对学生等年轻群体,或对这些内容有初步兴趣的人。虽然目前市面上类似的书非常多,但我觉得对学生或初入门的人群不一定都很合适,其中要么多是配合教学进程出版的、辅助性的书,目的性太强;还有一类篇幅太大,大概不太合适初学者。
我个人认为,现在孩子最大的问题不是学习得不够,而是过度学习。一个人成长需要虚实结合,你把他全部填满,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在做这套书的时候,我就想着量不要大,只要一本,做得有限一点、有趣一点。我们都有学习的经验,学的过程其实是经历不断地更新、淘汰、遗忘,所以量不代表什么。因此,我们将诗删到最后的263首,文章不足百篇——这可能是与其他选本在设想上很大的一个区别。
我在书中也写着,希望这套书可以成为一个观澜的平台,读者可能不一定“下海”,也可能只是看一看,但是怎样一个位置比较好?你带着他到海滩边从头到尾走一圈,走个几公里,当然可以看到很多,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精力与时间。
文汇报:我们注意到,您最早选择的是诗与文,之后再加上词的选本。为什么是这样的编排呢?
陈引驰:我一开始的设想就是诗与文。至于一开始为什么没有词,因为诗和词非常不一样,词最初就是音乐文学,表现的东西狭而深,基本面向情感,尤其是男女之情。后来词的范围扩大,比如苏东坡“以诗为词”,他的词作涉及了多方面的经验和情思。但是通过词去了解的苏东坡和通过诗文了解的苏东坡,说实话也不尽相同,他的诗文所展现出来的世界和生活,比词的要宽阔得多。鉴于词的特殊性,所以最初就只编注了比较纯粹的诗选。当然后来,应许多读者的要求,增加了词选——分开处理,或许能更好呈现词本身的特色和变化。
说到古文,则是阅读古典所必须通过的基本文类,不读古文,对传统的理解真的会有问题。毕竟诗、词都只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你要了解过去,读文章是基本的。你学习文言文法,培养古文的语感,必须要从古文阅读中获得经验。但古文相对诗也会难一点,市面上比较适合初学者的读本也少。
文汇报:能给我们谈谈您的选择标准吗?里头是不是或多或少包含着您的个人志趣或审美情趣呢?
陈引驰:选诗文,我有三点基本的想法:第一点,要美。这点对于今天尤其重要,如果是一些佶屈聱牙、很繁复纠结的东西,读起来很辛苦,为什么要让孩子读?美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接受的东西,放在今天可以化用。读这些诗文的过程就是在体会、汲取文字之美。
第二点是要古今沟通,选择的诗文起码对孩子来讲要比较容易理解,其中的基本感情、价值观念与今天还能吻合,不然反而可能破坏他作为现代人正在成长中的内心秩序。
第三点就是量不能多,少而精,如前边提到的,压缩到现在这个篇幅,一本足够。
选的这些诗、文、词,至少在我看来都是好的,我喜欢的。当然入选的并非不可替换,如果换一个人选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方向和面貌大抵就是这样吧。比如,李白的诗选得最多,是因为书的初衷是为孩子或初学者提供一个合适他们审美及理解范围的读本,李白的诗比较适合,但并不代表我认为李白的诗在诗歌史上最了不起——也就是说这几册选本,不是诗歌史、文章史或词史意义上的选本,而是提供人们培植基本古典文学素养的读本。
诗文选重在有平衡感和整体性
文汇报:古文早前也有非常通行的选本,像《古文观止》。您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样的选本怎么样?
陈引驰:《古文观止》其实是古时候给普通人的入门读本,代表了当时普遍的思想模式。但现在我觉得它实际上非常不合适孩子,或许是我个人的偏见,《古文观止》200多篇,适合初步接触古文的人读的大概就是30多篇。
特别是其中很多长篇大论、高头讲章,在当时非常重要,代表了一种思想潮流或那个时代读书人看重的东西,但无论是文章形式还是表达的思想感情及观念放在今天会有些不合时宜。
比如韩愈的《原道》。韩愈这个人非常重要——他是中唐时期的古文大家;这篇文章也是标志性的——当时思想高度多元,韩愈要提倡古文、复兴儒道、排佛老,这就是儒学转折关头的一篇文章。而他倡导的儒学复兴一直持续到宋明以后,就是理学或心学的兴起。这篇在过去当然也是名文,对于准备投身仕途的士子绝对有用,今天大学的文史专业里也教它、研究它。
但是不是要给小孩子读?我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一来,小孩子理解不了,二来,古今价值观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不太相信对一个刚接触古文的中学生来说,读《古文观止》是一个好的入门选择。
文汇报:您的选本就是很简单地按时间编排,是否曾经考虑过其他的编排方式呢?
陈引驰:我很反感分主题来讲古代的诗文。这些所谓主题,是随时代变化的,用主题来编诗文,实际上暗含了特定时代的价值观。许多书本尤其是流行的教科书,给孩子选读的内容往往不平衡,用的是任意的、拆碎的方式——今天让学生去读这个,明天读那个,但你仔细去看其中的诗文排序,是没有整体概念的。你可能会注意到难易差别,但更多的是编者觉得在这时候应该给学生灌输一个什么观念,所以在时代、整个脉络上都是无序而零散的。
需要提供另外一种选择。我并不是说这套书里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的,但起码这些诗文是在一个总体观察的基础之上得出来的。现在编一部诗选、文选并不难,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平衡感和一个整体性,也就是说,整体看下来,这些诗放在这里合不合适。
按照历史时段来编排,当然也会有问题。比如可能有人认为,一上来就是“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小孩子读不了。那么也可以让初学者从绝句、从最简单的唐诗入手,比如《唐诗三百首》开篇就是古体,初读其实不容易进去,从后边的绝句开始,大概是更好的选择。可能以后我们也可以在一部面向初学者的选本里面,尝试两个目录,一个是按历史时序的,另
一个目录呈现由浅而深的阅读次序?但我还是会给你提供这样一个版本,读者用几年时间陆陆续续读下来,会潜移默化形成自己系统的观点。
文汇报:为了实现这个整体感和平衡感,是不是会有一些被“牺牲”的诗文词?
陈引驰:这一点,诗非常明显。唐诗最多,但其实我个人对六朝的诗很有兴趣,许多却不能放进去,因为与我们选本的目标不契合。
我选择的都是现在大家已经熟悉的、经典化了的作品。这类作品语言形式比较规整,适合小孩去读。现在有些选本就想跟别人不一样,专找一些生僻的诗文。一开始我也希望选目上有些特点,最初划了七八百首诗,然后从中再选,选下来确实跟很多选本有重合,我开始还想这样好不好,后来觉得,这也是一种选择,不光是我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唐诗的经典化确实最为清楚,共同的认同最多。宋诗就要差一点,到元明清诗每个人的感觉就差别非常大。我和一起参与工作的两个学生也找了一些有名的选本来看,明清如果同一诗人各选5首,各部选本之间可能都没什么重合。这意味着这些诗的经典化程度不高,所以在选择时,还是经典化程度最高的唐诗入选数量最多。
文汇报:有人说,和科举时代不同,现在推崇的是叙事性比较强的、浑然一体的诗歌。您觉得我们今天对诗歌的口味有变化吗?
陈引驰:肯定不一样,但很难归纳,毕竟每个人的口味也不一样。陈世骧讲,中国文学有一个抒情传统,这个观点在台湾地区接受度很高,现在在更大范围里开始有影响。至于叙事性,现在也有学者在发掘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叙事传统。
读古诗,尤其对普通读者来说,很多还是“格言警句”、“名人名言”式的,诗里面一些特别的句子,觉得很美,就记住了。比如大家都会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是整首诗原来是什么意思,不一定真了解,有些可能是断章取义式地去理解。古典诗歌有一个自身的脉络,今天的一般读者或许多是“抽象继承”,“七宝楼台,碎拆下来”。
文汇报:市面上有些诗词普及书,往往带有较为浓烈的作者个人色彩。比如《蒋勋说唐诗》很受读者欢迎,但其中对时代的感悟或对诗词发展的看法不一定有研究基础,例如“唐代文学不是与南朝文学一脉相承,而是来自北方”……您怎么看这类普及呢?
陈引驰:我没怎么看过蒋勋的书,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对此很反感,觉得里面有些内容是讲错的。我想这个事情要分开看。如果他的目的是做一个大众普及,那么只要有他的想法,而且不是完全凭空而来的想法,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蒋勋本来是学艺术史的,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和感知力,我想他应该不会完全胡说。比如讲李白,会是李白大致的样子,只是讲到某个具体事情,或对它的具体理解,可能会错。
至于发挥,有时是要看对象的,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确实需要发挥。就拿我本人比较有兴趣的佛教文学、老庄道家来说,你以为佛经里面讲的都是“四大皆空”“苦集灭道”“八正道”这些抽象概念?其实佛经里很多都是讲譬喻故事的,所以陈寅恪先生曾概括有一类佛经是“例引故事以阐经义”,比如《百喻经》就是从不同经典摘出来的。佛教早期主要是口传的,传经的时候肯定要讲这些故事,利于大家理解,有益于推广。学者不必要特别苛求,大众如果接受,只要有了启发,不管丰富了知识还是情感世界,那就好,但是也要知道再往上走有不同的视野。
说唐诗不与南朝文学一脉相承,这个怕是随便讲的(我要克制我学者的立场)?他那样讲,是希望大家考虑国际性的因素、考虑游牧文化的影响?这可能也有道理,唐代确实是跟别的时期不一样。但认真来看,唐诗的形式就是南朝的,比如声律,近体诗无疑继承了南齐永明以来的探索成果。再比如边塞诗,实际上跟北方的传统没什么关系——岑参、高适写的边塞诗哪里是继承胡人的传统?最主要还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但换个角度来看,提醒大家唐代文学、诗歌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在里面,这个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蒋先生大概是在讲一件很笼统的事情,而不是以学者的态度跟你很严谨地论证这件事。
讲传统也一定要讲世界
文汇报:您怎么看待诗文的背和读?关于吟诵,叶嘉莹曾主张,传统的诵读不应该断,并且想要留下一套范式。
陈引驰:对待诗文有两点很重要:诗要背、文要读,这其实都跟声韵有关系。中国传统里,声音还是很重要的,两三岁的小孩子其实本身对诗的意思是不懂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如何理解?但这里面本身有一种声韵的和谐之美,他记住了那个声音,就能背下来。
文章是要读的,读出声来的。诵读还是很重要,古代讲到读,多是指大声读,从《庄子》到唐宋古文家,乃至桐城派都是如此,有时高声朗诵,有时轻轻地读,有一套讲究在里面。除了声音,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就是文章的“气”,也就是文章的脉络。古时人们不用标点,读了才知道一篇文章什么地方应该断、什么地方要慢,什么地方不太重要应该赶快过去,这些都是帮助理解的。
现在也是,有时我们专业的研究生考试就拿一段没有标点的古文请考生读一读,如果读下来大致不差,就说明你懂了。读、背很重要,包括学英语的经验也是如此,我中学时老师教《新概念》英语,那时条件没有现在好,就是很大的一台录音机抱来往讲台上一放,让我们不断复述其中的句子,复述就知道它大概在说什么,起码“音”先抓住了。复杂的句子有从句,从哪里开始读,读起来轻重缓急就很清楚,包括对整个语言的感觉,对理解意义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套历史经验不是说绝对是对的、绝对有效,但还是有道理的,看你怎么用。
文汇报:诵读时有必要用读书音吗?
陈引驰:这样培养音律感太辛苦了,现在小孩的学习多多少少还是要讲点效率的,我觉得这个效率不高,有点太技术,体会五言七言中的平仄交错就够了。甚至更进一步说,一个人说话结结巴巴有什么不可以,一个人说得快或慢一点有什么不可以?一般人不需要这种训练,读诗知道平仄是怎么回事,有个整体的感觉就行了。有诗的声律知识当然是好的,但是技术化没有什么必要。
文汇报:在您看来,古诗文和它背后的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应该占一个怎样的位置?
陈引驰:我一直持这个想法,讲传统也一定要讲世界,要放在一个大环境里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的 “国学”,过去实际上是指国家的教学和学术机构,到了近代,借用了日本的讲法,才开始泛指跟自己传统相关的那些思想文化学问。这是一个在比较的、世界的视野当中才有的概念。
因此,传统的学问或者国学只是大环境下给你提供的其中一种选择或资源。所谓传统,很多人认为是从过去到现在的,包括很多人对“传承”有焦虑,但实际上传承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这就如时间是条河流,决定是不是利用水流来建水库不是上游的人,而是下游的人。事实上,传统是被后来认同的,认了以后不断地被思考。
有一种说法,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的解读,就是说认了柏拉图,不断地让他的学说在这个传统里面经历各种辩证而发展。中国的传统也是这样,儒家、道家这些“百家争鸣”的“家”,是汉代才有的概念,先秦所有的文献都是讲“子”。也就是说,成“家”是后来的事。所以,后来人对“传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站在时间的下游,认同这样一个传统,确立这样一个脉络。用时髦的话来讲,传统就是后来人建构出来的。
文汇报:所以说,您觉得现代人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和资源,是吗?
陈引驰:我相信既然是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又是本民族本文化的东西,总是有人愿意去了解,如果里面再能够吸取一些新的东西,承而后创,把它接续下去,那自然更好。但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这样做。也有另外一种人,完全排斥传统,他脑子里是另外一种文化,魂飞天外,梦萦天际,这也没什么不可以。
比如现代文学里面,有几位我非常喜欢的诗人,像何其芳,诗和散文都写得很漂亮,他对传统比如词也很有了解;早年写白话诗,到晚年开始写旧体诗,回归传统,这是一种选择。穆旦,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很深,他的诗始终与传统没有多少关系;上世纪50年代归国后,开始翻译,比如《唐璜》《欧根·奥涅金》,就是不回到传统,这是他的选择。再比如冯至,受里尔克的影响,研究歌德,但他也写《杜甫传》,还编杜甫的诗。我的意思是说,从个人来讲,每个人做什么样的文化选择都是合理的,只要对他来讲,能找到让自己安心的精神世界。
就我来编这几本书来说,展示给你,你接受与否是你的选择,我认为个人的每个选择都没问题,而且都可以是好的选择;但就整体格局而言,我提供这样一种可能性是非常必要的:第一,它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第二,它也是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尝试为后人提供一种选择的资源,如果觉得好,就请认同、继承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