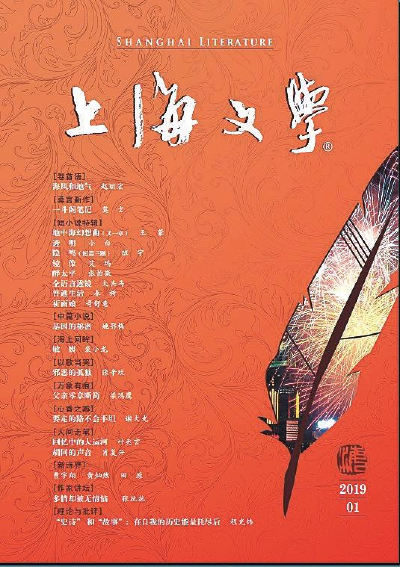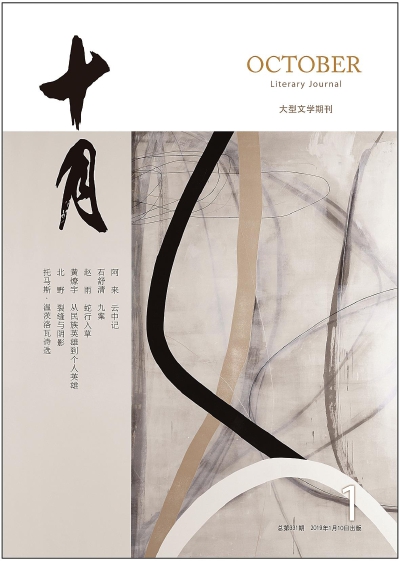■本报记者 许旸
2019年开年,作家们献给新年的第一个故事有哪些?记者获悉,多位名家的新作集中亮相《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纯文学期刊,对时代做出文学的呼应。
其中尤其亮眼的是,冯骥才时隔多年重返“小说现场”,以一段跨国恋情探讨中西文化碰撞,独特的津味书写再续“怪世奇谈”;老将王蒙、莫言、刘庆邦、迟子建笔耕不辍,纷纷带来最新短篇小说,令“短”的美学得到更多面向的创作实践;叶兆言、阿来则转向真实的历史和时代事件,打造了创作脉络中的不容忽视的标志性代表作,拓宽了中国故事书写的维度。
这些故事并不惮“剧透”,文学依然展现了极具弹性的阐释空间。
沉淀近30年再度出手,延续冯式津味
“有朋友问我是不是重返文坛、迎来创作的‘第二次浪潮’?我能肯定的是,我正重返小说。”近15万字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在77岁作家冯骥才心中孕育了30年。小说首发于今年第一期《当代》,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故事发生在19世纪津门地区,1862年之后,天津建立英法租界,成为历史上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于是,一段跨国恋情,沉醉于悲怆的历史河流中,小人物的爱恨情仇,演绎着那个时代中西文化历史碰撞下的命运悲剧,并在更深层次反映了两种文明相互的误读、猜疑、隔阂。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意象,单筒望远镜意味着“使用它只能用一只眼,有选择地看对方”,变身150多年前文化对视的绝妙象征——世界是单向的,文化是放大的,现实就在眼前,却遥远得不可思议。
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后,《单筒望远镜》是“怪世奇谈”系列的一部新作,也是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冯骥才多向度全景式书写了天津地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群体人格,延续了冯式独特的津味,将斑驳历史再次拉入记忆中,百年多前的天津风貌跃然纸上。冯骥才说:“在历史上,天津地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那个时代天津城市空间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老城、一个租界,使这个城市的历史、形态、生活文化,与中国其它任何城市都不同。”
《当代》杂志副主编杨新岚将《单筒望远镜》形容为“一部有着强烈命运感的小说”,“从一个人到一座城再到一个国,百年前的静美和惨烈以文学的方式导入我们的文化记忆。在剧烈的冲突当中,作品承继了孙犁荷花淀派的风格,写出了美,更写出了残酷。”上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投入大量精力从事文化遗产保护。“20多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中止了文学创作,反过来于我却是无形的积淀与充实。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加上这么多年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累积,现在写起来挺有底气的。”
精悍篇幅里筑造人间百态,探索小说极简美学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多家文学刊物推出了“短小说专辑”“短篇一组”等专栏,让人们再次领略短篇的魅力。其中,王蒙、莫言、迟子建、刘庆邦等作家都推出了中短篇小说新作。
年过八旬的王蒙“花开两枝”——今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分别首发了他的5万字中篇小说《生死恋》和短篇《地中海幻想曲》(又一章),主题都是爱情。
《生死恋》的时空从北京胡同的院子辗转到世界多地,连着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的中国。“情感和血脉、空间和时间的温软、冷硬,全都攸关生命本该有的悲喜忧欢。可是道理说出轻巧,真真切切发生在人物和他们之间的过程,在《生死恋》貌似轻快的语调之下,回旋着沉郁顿挫、无法释怀的人生咏叹。”《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如是评价。
《地中海幻想曲》(又一章)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既有世道沧桑,更有强烈的生命活力。小说女主角隋意如有显赫的家世、学历、荣誉等,却在谈婚论嫁上屡屡触礁,小说以意识流写法讲述了她登上地中海幻想曲号邮轮后的旅行经历。读者在短小精悍的故事篇幅里,仿佛跟随40岁的她遍览人生沿途风景,令人感叹王蒙笔力之老辣精准。
着迷于短小说美学的还有莫言,他的《一斗阁笔记》首发于《上海文学》今年第一期,含12篇短小说,最短的200多字,长的不过400来字,依然是写家乡高密,古代传说交织童年记忆,穿插了形形色色的乡间人物故事。这12则故事让人联想起《聊斋》《阅微草堂笔记》,却又完全不同于古人,而是当代作家对家乡,对土地,对世俗人性的描画。《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说,短篇小说如何写得精短耐读,以极简篇幅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并给读者联想和启迪,对作家提出了极大挑战。
刘庆邦最新短篇《到外面去睡》首发于《江南》今年第一期,小说写了一段别样的青春记忆,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几个乡村青年,通过离开家、夜里到外面去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独立、叛逆以及对摆脱管束的渴望。那些曾被时代和环境禁锢的青春心灵,在广阔无垠的幕天席地中,尽情释放自我,挥洒年轻多余的精力,以此寄托对外面世界与自由的强烈向往。
以文学的方式为一座城市立传,为时代留影
在中国作家中,叶兆言不是唯一一个,却是许多读者公认写南京最多也颇具特色的当代作家。近年来,他的文学雄心就是写一部非虚构长篇《南京传》,现已完稿,预计今年内出版单行本,而书中章节 《应天府——〈南京传〉之大明王朝》首发于《花城》今年第1期,能让读者们先睹为快。
有着2500多年建城史的南京,市井里巷尽染六朝烟水气,引得无数后人歌而咏之争而写之。“显然要描述南京历史,展现南京文化,给这座悠久的城市树碑立传,并非易事。”这一次,叶兆言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更是在历史故纸堆中浸泡多年的考据者,从岁月长河中打捞线索,寻找那些被忽略遮蔽的细节。
同样酝酿多年文学果实的,还有作家阿来。继2008年长篇小说《空山》后,阿来20多万字长篇新作《云中记》首发于《十月》2019年第一期,单行本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将文学聚光灯投向11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灵,山外世界的活力和喧嚣,交织成意义纷呈的多声部回响。“重大现实题材并不好写。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个消失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写出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尊重,而不是停留在灾难表面。”
关于《云中记》,阿来坦言这部作品“献给地震中失去宝贵生命的人们,献给消失的村庄,献给抗震救灾中的英雄们。”阿来说,当年地震发生后,他曾多次自驾去受灾现场,“面对巨大的创痛,我说不出什么话来,说什么也表达不了我的心情。那时我觉得只有莫扎特《安魂曲》适合我的心情,用车载CD在现场一遍遍播放。《云中记》也是在这首庄重悲悯的吟唱陪伴下写就的。”
“十年前,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阿来曾声称不能轻易触碰,这种态度证明了作家对生命价值和创作的虔诚敬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评价,阿来并非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仅凭一腔热血投入写作,而是经过长久的沉淀,从天灾思考书写创伤的修复、灵魂的抚慰,终于找到了独特的切入口和表达方式,体现了文学的高贵与有尊严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