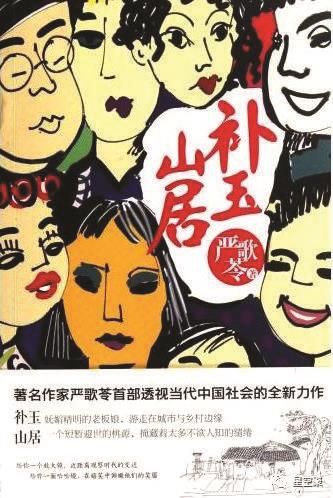张成
美籍华裔作家严歌苓的小说《补玉山居》六年前在中国大陆出版。不久前,根据其改编的电视剧《你迟到的许多年》播出,成为重读该小说的契机。在重读的过程中,小说对中国城乡生活、个体经验与社会变迁的似是而非的描述,以及沿着小说情节敷演而来的美学、生活逻辑与六年后今天的世事实情相遇,其荒腔走板便愈发显眼。
《补玉山居》被称为“当代中国的‘新龙门客栈’”,满满的江湖气息,自然而然地激活了笔者观赏胡金铨执导的《龙门客栈》、徐克监制的《新龙门客栈》的经验。在这两部“客栈”里,有道义与奸邪的对决、有长情的江湖儿女、有琐屑又野趣横生的人情世故与江湖仪轨……总体而言,这两部“客栈”是富含民俗文化的快意恩仇录,它的情感指向是类似地摊文学的。《补玉山居》借用了“客栈”——补玉山居的意象空间,以老板娘曾补玉为经线串起四个传奇故事,某种程度上很容易激发读者的地摊文学式的想象。
“地摊文化”有一个漫长的雅化的过程,如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致敬同名文类,并在戛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小说《罗曼蒂克消亡史》以纯文学的方式改写稗官野史,更不用提莫言对“茂腔”等戏曲文类的化用等等……换句话说,民俗文化、地摊文学等接地气的文艺元素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内生动力。
《补玉山居》试图用纯文学的叙事方式来驾驭四段地摊文学的素材,每段故事的选材都极致、传奇、噱头十足。同时,《补玉山居》还作出了摹写中国城乡变迁的姿态,在实际操作层面却远谈不上精准,反而错讹百出,只是展现了作者想象中的中国城乡;如果把《补玉山居》当作真正的地摊读物来看,它又匮乏那种灵动、野性、充满活力的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刺激性。
无论是在表现世界、还是在改造世界层面,《补玉山居》都不是一个合格的文本。它无意于与世界对话,人物是概念式的符号,社会环境不具有烟火气,在此基础上的价值表达往往流于空洞的概念甚至常识。退一步,如果《补玉山居》不打算与世界对话属于文学的自由,那么在叙事层面,它不应该言之凿凿地刻薄、漫画化弱势群体。而且,尽管严歌苓使用了大量的间接引语,但略显粗糙,“隐含作者”的声音经常闯入人物的声音,导致叙事视角的混乱——至少在技术层面,《补玉山居》还大有打磨的余地。
《补玉山居》里的曾补玉及村民,只是一个想象中的农村符号,他们并没有被提炼出所谓的人性。原因无他,人性从来不是空洞的,它必然带有社会文化及属性的烙印,同时这种社会文化和社会属性也决定了人的情感脉络。《补玉山居》定位在北京京郊,但完全抽空了北京人独有的文化和情感特征。曾补玉的精明能干与爱好八卦更像是人物的标签,而这种空洞的标签既可以是一个四川客栈老板的,也可以是一个上海客栈老板的,曾补玉并不是表演术语形容的“这一个”,人物始终没有立起来。胡金铨在 《老舍和他的作品》一书中,曾提到北京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具有一种独特的从容和幽默,如顾客吃饭的时候抱怨菜不好吃或者咸了,店小二除了会立刻处理菜品,同时还会虚构一个“昨天厨房大师傅和老婆吵架了,心情不好”的小段子,来解释为什么菜会咸,这既说明了菜品失水准的偶然性,又以一种人之常情让顾客会心理解。不管是《茶馆》中王利发的世故、分寸,还是类似的北京市井小民的 “尊傲”“热心肠”这样的“独占”标识,在曾补玉身上几乎没有。
当然,写北京农民,未必一定按照老舍等京味作家的角度和价值观来写,但是起码应该立足于其社会的文化的基本实情,而不是以看似写实,实则架空的方式“伪写实”。《补玉山居》中的其他村民形象也仿若游戏中的NPC,或者说仿若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亚裔活道具,村民的灵魂与生活的本来面貌在《补玉山居》里无足轻重,它们只是传达一种理念的提线木偶和推进剧情的群众演员。
人物立不起来,小说就没有生命。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小说尚未写完,但安娜的死亡结局早已注定,就在于安娜早已具有了独立的生命和人格,不管托尔斯泰愿不愿意,她都将按照小说和人物的逻辑走向卧轨。而《补玉山居》似乎没有这样严密又如其所是的文学、生活逻辑,它的总体思维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浪漫地以一方之极端去反衬另一方,如为了突出冯焕与彩彩感情的真挚,就要贬低冯焕与所有人的关系;为了突出老张与文婷的爱情,就要突出儿女的不孝和精神病院医生的玩忽职守;为了突出曾补玉的精明能干,就要突出村民群氓无赖……因此,作为背景板的负面人物没有充实的灵魂和声音,只需作好负能量的蓄能。
正是在上述的审美主导下,《补玉山居》的很多描写是脱离了现实的。小说中,曾补玉的同乡在大约2006年左右抛家舍业去南方当保安,月入千余元,他的家人为此而面露“幸福”表情。当然,不排除有这样的个案,但从常识来看,这与生活的真相不符。当大量类似的与现实逻辑不符的桥段堆积一起时,则导向了那个与现实无关的极端情境。某种程度上《小时代》也追求类似的极端、极致,但《小时代》限定在一个极小的浮夸圈子中,读者会有保持阅读距离的心理预期,但《补玉山居》中较为常见的“城乡”“农民”等元素容易给人一种普遍的、写实的错觉。严歌苓在描写冯焕的属下时,显然不能理解年轻人对上司真心拥抱与逢迎的复杂现实,因此,只能铺陈陈词滥调;为了突出彩彩的高洁,就以“土”来贬低仲夏;当彩彩面对北京地标之一隆福寺的时候,作者替她甩出一句“好难看的一片视野”这种既不符合人物身份、又疑似病句的心理独白,然后转入避实就虚的情感描述。姑且不论,彩彩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来过北京的女孩儿,当她面对市井气息浓厚的隆福寺时,沉浸在《补玉山居》中所描写的仙女般的、不谙俗物般的自说自话的情绪里,逻辑上是否合理,单从叙事手法上看就落了下乘——当主体面对“陌生”的场景时,主体的反应最容易出好戏,比如是枝裕和在《无人知晓》里,塑造了一段哥哥搵食时打球的戏,在那段戏里,他从一个养家糊口的“男人”又变成了一个孩子,让人看到正是哥哥在本该像其他孩子一样在球场上玩耍的年纪,却承担了本不该承担却又不得不承担的生活重担,是枝裕和通过这样一个“欢乐的跑题”又回到了主题,更加震撼人心。与《补玉山居》里的这段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严歌苓的作品成为很多大导演热衷于改编的IP,或许就在于她擅长在小说中提供一个极端、惹眼的故事外壳和素材,行文中漫画化的视觉构造、反讽的语调和乍看接地气的世故容易让人形成直观的感觉和形象,从而忽略了文学本体上存在的问题。《补玉山居》有一种文化归属与细节描述的双重失焦,是因为作者对所写地方的风土人情不熟悉,更缺少爱。相比之下,极度聪明的作家如张爱玲、汪曾祺都看透了人世凉薄,但在其小说中,总有一种更高的苍凉的视点来协调人的不完美、缺点,让读者产生一种会心的和解。毕竟,反讽与刻薄不应该是作家的目的,而是抵达敦厚与包容的渡桥。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学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