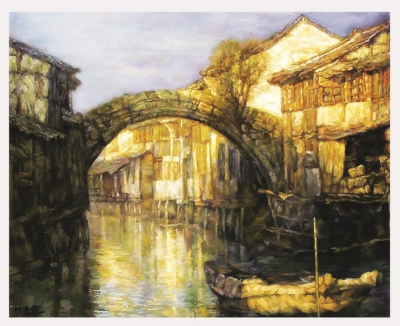■孙琴安
早在80多年前,卞之琳与何其芳、李广田三位青年诗人合出了一本诗集《汉园集》,遂有“汉园三诗人”之称。后来李广田、何其芳二人相继去世,我曾对卞之琳开玩笑说:“汉园三诗人中,数您的寿命最长。”他笑了。没想到在新世纪将临之际,他也去世了,终年90岁。
以往我每次去北京,总要到卞先生家去,而所谈的又总是诗。每次去,卞先生几乎都是在案边写作或看书,屋里总是很安静。我知道卞之琳与何其芳都很注意诗的形式,曾一度探讨过新格律诗的问题,在译诗中也很注重格律,但我的观点与他很不相同。
记得30多年前有一次在卞先生家,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班门弄斧,在他面前大谈诗的形式和格律:“不论中外,人类格律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诗歌不可能永远是格律诗,20世纪实际上是以自由诗为主的时代,就是再提倡格律和新格律诗也没用。”为了自圆其说,我不断举例,竟然说了十几分钟。卞先生居然静坐着听我讲完,也不插话,而且听得非常认真。我知道自己的这个观点与他相左,便等他反驳。不料他听完了却点点头,说:“你的这个观点还是有点道理的。”“真的吗?”我一阵惊喜,又有点怀疑。“真的。”他又肯定地点点头:“是有点道理的。”
此情此景,我至今记得。因为我知道卞之琳在学术观点上轻易不附和、不含糊,而今居然赞同一个年仅30多岁又名不见经传的后辈的意见,这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一阵。
有一次去北京,正逢国庆节前夕,住宿紧张,我和一位同事暂住北京师大,需补办手续方可长住。情急之下,我冒昧地去找卞先生,他连忙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托我转给该校蓝棣之,在他的帮助下,总算安居了下来。几天后我去卞先生府上致谢,又谈起了诗。当时他为了找一份有关诗的材料,在他的大写字桌上乱翻,我见桌上书籍纸张凌乱,怕他找不着,就劝他别找了。没想到他一会儿就翻了出来,一边拿给我,一边指着杂乱的书桌笑着说:“我这是杂而不乱,自有条理,什么东西放何处,只有我知道。”
交谈时我说:“诗人臧云远也到延安去过,并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您,说在延安时也曾碰到过您。”卞之琳是个很认真的人,他听后想了一会儿,然后说:“这篇文章我没见过,如你方便,我倒想看一下。”回沪以后,我就把臧云远文章中有关卞之琳的内容复印了一份寄给了他。他接到后,在1991年6月23日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承费神复印寄来臧云远文有关一段,谢谢!我应约写的一篇小文已寄出,现对照臧文,似没有记得太错的地方。只是上了年纪,除非当时记有日记之类,回忆过去总不免有出入处,我已不大记得在延安见过臧了。说我“一身八路军打扮”,显然当时我刚从前方回来,是在春夏时,还没有来得及换夏装。他说我“三二年、三三年在北大西斋穿蓝布大褂”,倒像是何其芳的样子,他住过西斋,后来方敬也住过那里,李广田和我住过东斋,我都不记得和臧在沙滩见面了,却记得1935年清明时节在日本东京和他见过一面。
你的文章,还未见北京有复印件寄来,但没有关系,等发表后再看吧,我相信没有什么可订正的地方。
有关他与臧云远见面的问题,说实话,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卞先生在信中作了这么一番追忆,其态度之认真,由此也可见一斑。
后来我写毛泽东与作家交往的书,想起何其芳在文章中曾写过他与卞之琳、沙汀在延安同见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交谈的事,心想卞之琳还在世,延安可能只是他早年见过毛泽东的地方,也许他后来还在别处见过,便给他写了封信求证。卞先生在百忙中立即给我回了封信,信中说:“近半年来,事繁心烦,时间精力,两都不济,案头来信山积,实在无法一一清理置答。三月十六日来信,因素厌事实以误传误,这次涉及的人物又非同一般,有关与我的微末接触,亟需澄清,特抽空答复几句。”
接着,他就以较长的篇幅,回忆了他见到毛泽东的几次情况。尽管他作了补充,但他在信的末尾,还是善意地劝我:
虽然我现在补充告诉了你这些细节(多半是记不准的),我还是奉劝你不要在这方面写什么文章,因为这些都无关紧要,也乏善可陈,我也不愿意藉此给自己脸上贴金,藉此招摇。说话、写文章,都要认真,随便不得,查对材料,更应有真凭实据,实事求是,你在研究所工作,当然理解,用不着我提醒。
当然,我还是谢谢你的好意。
像这样奉劝我不要撰写毛泽东与文化名人交往的前辈作家有好几位,他们或认为意义不大,或认为风险太大,很可能吃力不讨好,除卞之琳以外,臧克家、柯灵、冯至等似乎都有这个意思。但我顾不了这些忠告,总想为后人留有一些可资参考的有价值的历史真相,所以仍一意孤行,最后终于撰成了一部82万字的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分上下两册出版,并寄给了卞之琳一套。他收到以后,在1994年3月24日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毛泽东与名人》早收到,谢谢。作为‘名人’,且列入这本书中,实在不配,深感不安。幸所记事实,尚无太大差错,也就搁在一边,待有空再读其中各文。……岁尾年头,偏又以低效率赶履行几项文字承诺,所以接书也就没有即复道谢,请谅。”
也是在这封信中,卞之琳还谈起了自己近年来的生活状况,他写道:“年迈体弱,一年来仅两次出门活动,一次在去年二月下旬闻冯至病危前往医院探看,另一次九月间往艾青家会美国来的叶维廉。去年二月一日,照平时惯例以亲自上下四楼至传达室取邮件,作为锻炼,取晚报回来,在二、三层之间摔伤,幸仅破及颅骨外皮,缝了五针,一周后也就没有事了。但家里人再不让我下楼了……”在信的结尾,他又写道:
我倒想起你前些年出版过一本现代几个写诗的作品赏析集子,我是保存的,只是一时忘记堆藏在什么地方了。不记得其中有无谈我《断章》一诗的,我正帮助友人收集关于此四行短诗的妙解、歪解、乱解的材料,如有便请抄录你自己的几句话,就要发表过的,不要现在新写,寄我备用为感。
每读此信,在我的眼前便会出现一位白发苍苍的戴眼镜的老者,迈着细碎的步子,微颤着身子在房间里拿书取报,或伏案写作,或娓娓而谈……现在,这位老人已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断章》《圆宝盒》却留存了下来,而且,恐怕是会永远留传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