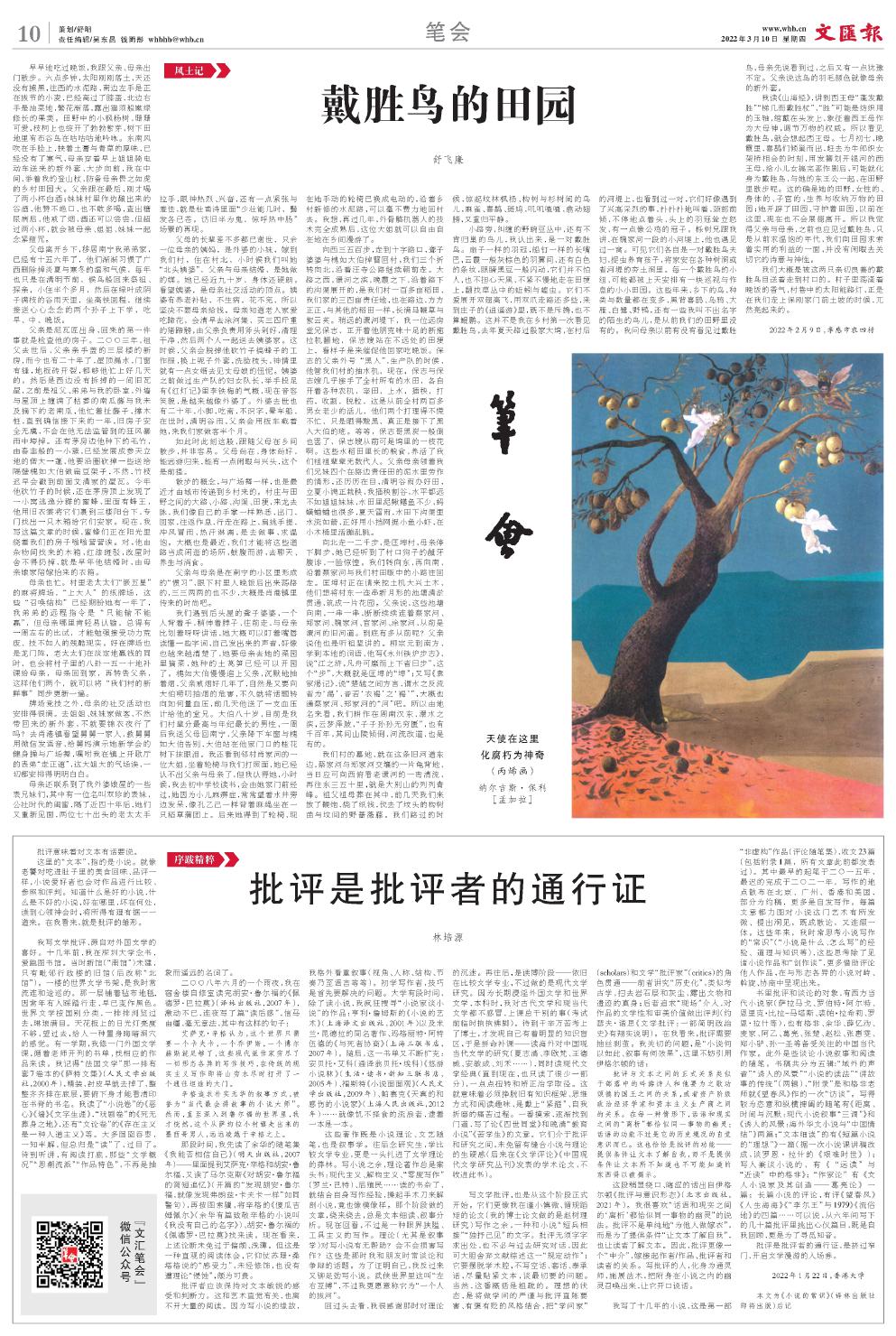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2-03-10 第27,164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戴胜鸟的田园
舒飞廉
早早地吃过晚饭,我跟父亲、母亲出门散步。六点多钟,太阳刚刚落土,天还没有擦黑,往西的水泥路,南边左手是正在拔节的小麦,已经高过了膝盖,北边右手是油菜地,繁花渐落,露出猫须般嫰绿修长的果荚。田野中的小枫杨树,珊珊可爱,枝柯上也绽开了勃勃紫芽,树下田地里有布谷鸟在咕咕咕地吟咏。东南风吹在手脸上,挟着土膏与青草的厚味,已经没有了寒气,母亲穿着早上姐姐骑电动车送来的新外套,大步向前,我在中间,举着我的登山杖,防备母亲畏之如虎的乡村田园犬。父亲跟在最后,刚才喝了两小杯白酒;妹妹村里作坊酿出来的谷酒,他赞不绝口,也不敢多喝,查出糖尿病后,他戒了烟,酒还可以尝尝,但超过两小杯,就会被母亲、姐姐、妹妹一起念紧箍咒。
父母离开乡下,移居南宁我弟弟家,已经有十五六年了,他们渐渐习惯了广西删除掉炎夏与寒冬的温和气候,每年也只是在清明节前,候鸟般回来祭祖、探亲,小住半个多月,然后在绿叶成阴子满枝的谷雨天里,坐高铁回程,继续接送心心念念的两个孙子上下学,吃早、中、晚饭。
父亲是泥瓦匠出身,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他的房子。二〇〇三年,祖父去世后,父亲亲手盖的三层楼的新房,而今也有二十年了,屋顶漏水,门窗有缝,地板砖开裂,都够他忙上好几天的。然后是西边没有拆掉的一间旧瓦屋,之前是祖父、弟弟与我的卧室,外墙与屋顶上缠满了枯萎的南瓜藤与我未及摘下的老南瓜,他忙着扯藤子,撑木桩,直到确信接下来的一年,旧房子安全无虞,不会在他无法监管到的狂风暴雨中垮掉。还有茅房边他种下的毛竹,由春韭般的一小簇,已经发展成参天立地的偌大一蓬,他要沿圈砍掉一些送给隔壁槐如大伯做扁豆架子,不然,竹枝迟早会戳到前面艾清家的屋瓦。今年他砍竹子的时候,还在茅房顶上发现了一小窝逃逸分群的蜜蜂,里面有蜂王,他用旧衣裳将它们裹到三楼阳台下,专门找出一只木箱给它们安家。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蜜蜂们正在阳光里绕着我们的房子嗡嗡营营诶。对,他由杂物间找来的木箱,红漆斑驳,改屋时舍不得扔掉,就是早年他结婚时,由母亲娘家陪嫁抬来的衣箱。
母亲也忙。村里老太太们“嵌五星”的麻将牌场,“上大人”的纸牌场,这些“召唤结构”已经期盼她有一年了,我弟弟的远程指令是“只能输不能赢”,但母亲哪里肯轻易认输,总得有一周左右的比试,才能勉强接受功力荒废、技不如人的残酷现实。好在牌场也是龙门阵,老太太们在淡定地赢钱的同时,也会将村子里的八卦一五一十地补课给母亲,母亲回到家,再转告父亲,这样他们两个,就可以将“我们村的新鲜事”同步更新一遍。
牌场竞技之外,母亲的社交活动也安排得很满。去姐姐、妹妹家做客,不然带回来的新外套,不就要锦衣夜行了吗?去肖港镇看望舅舅一家人,教舅舅用微信发语音,给舅妈演示她新学会的健身操与广场舞,嘱咐我在镇上开歌厅的表弟“走正道”,这大姐大的气场诶,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母亲还联系到了我外婆娘屋的一些表兄妹们,其中有一位名叫双珍的表妹,公社时代的闺蜜,隔了近四十年后,她们又重新见面,两位七十出头的老太太手拉手,眼神热烈、兴奋,还有一点紧张与羞怯,就是杜甫诗里面“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场景的再现。
父母的长辈差不多都已谢世,只余一位母亲的姨妈,是外婆的小妹,嫁到我们村,住在村北,小时候我们叫她“北头姨婆”,父亲与母亲结婚,是她做的媒。她已经近九十岁,身体还硬朗。看望姨婆,是母亲社交活动的顶点。姨婆有养老补贴,不生病,花不完,所以坚决不要母亲给钱,母亲知道老人家爱吃蹄花,会清早去涂河集,买三四斤重的猪蹄髈,由父亲负责用斧头剁好,清理干净,然后两个人一起送去姨婆家。这时候,父亲会脱掉他砍竹子搞蜂子的工作服,换上呢子外套,洗脸梳头,神情里就有一点女婿去见丈母娘的忸怩。姨婆之前做过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举手投足有《红灯记》里李铁梅的气概,现在音容笑貌,是越来越像外婆了。外婆去世也有二十年,小脚,吃斋,不识字,晕车船,在世时,清明谷雨,父亲会用板车载着她,来我们家做客半个月。
如此时此刻这般,跟随父母在乡间散步,并非容易。父母尚在,身体尚好,能远游归来,能有一点闲暇与兴头,这个是前提。
散步的概念,与广场舞一样,也是最近才由城市传递到乡村来的。村庄与田野之间的大路、小路、沟渠、田埂,来龙去脉,我们像自己的手掌一样熟悉,出门,回家,往返作息,行走在路上,肩挑手提,冲风冒雨,热汗淋漓,是去做事,求温饱。大概也是最近,我们才能将这些道路当成闲逛的场所,鼓腹而游,去聊天、养生与消食。
父亲与母亲是在南宁的小区里形成的“惯习”,眼下村里人晚饭后出来荡路的,三三两两的也不少,大概是肖港镇里传来的时尚吧。
我们遇到后头屋的聋子婆婆,一个人背着手,稍伸着脖子,往前走,与母亲比划着呀呀讲话,她大概可以盯着嘴唇读懂一些字词,自己发出来的声音,好像也越来越清楚了,她要母亲去她的菜园里摘菜,她种的土莴笋已经可以开园了。槐如大伯慢慢追上父亲,沉默地抽着烟,父亲戒烟好几年了,自然是又要向大伯唠叨抽烟的危害,不久就将话题转向如何量血压,前几天他送了一支血压计给他的堂兄。大伯八十岁,目前是我们村辈分最高与年纪最长的男性,一周后我送父母回南宁,父亲降下车窗与槐如大伯告别,大伯站在他家门口的桂花树下抹眼泪。我还看到邻村肖家河的一位大姐,坐着轮椅与我们打照面,她已经认不出父亲与母亲了,但我认得她,小时候,我去初中学校读书,会由她家门前经过,她因为小儿麻痹症,常常望着水井旁边发呆,像孔乙己一样背着麻绳坐在一只稻草蒲团上。后来她得到了轮椅,现在她手动的轮椅已换成电动的,沿着乡村新修的水泥路,可以毫不费力地回村去。我想,再过几年,外骨骼机器人的技术完全成熟后,这位大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乡间漫游了。
向西三五百步,走到十字路口,聋子婆婆与槐如大伯掉臂回村,我们三个折转向北,沿着汪寺公路继续朝前走。大路之西,澴河之滨,晚霞之下,沿着路下的沟渠展开的,是我们村一百多亩稻田,我们家的三四亩责任地,也在路边,方方正正,与其他的稻田一样,长满马鞭草与紫云英。稍远的澴河堤下,我一位远房堂兄保志,正开着他朋克味十足的新拖拉机翻地,保志嫂站在不远处的田埂上,看样子是来催促他回家吃晚饭。保志的父亲外号“黑人”,生产队的时候,他管我们村的抽水机,现在,保志与保志嫂几乎接手了全村所有的水田,各自开着各种农机,宰田,上水,插秧,打药,收割,脱粒,这是从前全村两百多男女老少的活儿,他们两个打理得不慌不忙,只是晒得黢黑,真正是接下了黑人大伯的班。等等,保志哥黑炭一般倒也罢了,保志嫂从前可是塆里的一枝花啊。这些水稻田里长的粮食,养活了我们祖祖辈辈无数代人。父亲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四个在路边责任田的泥水里劳作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清明谷雨办好田,立夏小满正栽秧,我插秧割谷,水平都远不如姐姐妹妹,水田里泥鳅鳝鱼不少,蚂蟥蛐蛐也很多,夏天雷雨,水田下沟渠里水流如箭,正好用小挡网捉小鱼小虾,在小木桶里活蹦乱跳。
向北走一二千步,是匡埠村,母亲停下脚步,她已经听到了村口狗子的龇牙腹诽,一脸惊惶。我们转向东,再向南,沿着蔡家河与我们村田畈中的小路往回走。匡埠村正在请来挖土机大兴土木,他们想将村东一连串新月形的池塘清淤贯通,筑成一片花园。父亲说,这些池塘向南,一串一串,断断续续连着蔡家河、郑家河、魏家河、官家河、涂家河,从前是澴河的旧河道。到底有多从前呢?父亲说他也是听祖辈讲的。柳宗元到南方,学到本地的词语,他写《永州铁炉步志》,说“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这个“步”,大概就是匡埠的“埠”;又写《袁家渴记》,说“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为‘渴’,音若‘衣褐’之‘褐’”,大概也通蔡家河、郑家河的“河”吧。所以由地名来看,我们耕作在周南汉东,澴水之滨,云梦泽陂,“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有千百年,其间山陵倾倒,河流改道,也是有的。
我们村的墓地,就在这条旧河道东边,蔡家河与郑家河交壤的一片龟背地,当日应可向西俯看老澴河的一弯清流,再往东三五十里,就是大别山的列列青峰。祖父祖母葬在其中,前几天我们来放了鞭炮,烧了纸钱,伐去了坟头的构树苗与坟间的野蔷薇藤。我们路过的时候,惊起坟林枫杨、构树与杉树间的鸟儿,麻雀、喜鹊、斑鸠,叽叽喳喳,翕动翅膀,又重归平静。
小路旁,纠缠的野豌豆丛中,还有不肯归巢的鸟儿,我认出来,是一对戴胜鸟。扇子一样的羽冠,船钉一样的长嘴巴,云霞一般灰棕色的羽翼间,还有白色的条纹,眼睛黑豆一般闪动,它们并不怕人,也不担心天黑,不紧不慢地走在田埂上,翻找草丛中的蚯蚓与蝗虫。它们不爱展开双翅高飞,用双爪走路还多些,来到庄子的《逍遥游》里,既不是斥鴳,也不算鲲鹏。这并不是我在乡村第一次看见戴胜鸟,去年夏天路过殷家大塆,在村后的河堤上,也看到过一对,它们好像遇到了兴高采烈的事,扑扑扑地叫着,颈部前倾,不停地点着头,头上的羽冠耸立怒发,有一点像公鸡的冠子。栎树兄跟我讲,在魏家河一段的小河堤上,他也遇见过一窝。可见它们各自是一对戴胜鸟夫妇,捉虫养育孩子,将家安在各种树洞或者河堤的夯土洞里。每一个戴胜鸟的小组,可能都被上天安排有一块巡视与作息的小小田园。这些年来,乡下的鸟,种类与数量都在变多,黑背喜鹊、乌鸦、大雁、白鹭、野鸭,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陌生的鸟儿,是从前我们的田野里没有的。我问母亲以前有没有看见过戴胜鸟,母亲先说看到过,之后又有一点犹豫不定。父亲说这鸟的羽毛颜色就像母亲的新外套。
我读《山海经》,讲到西王母“蓬发戴胜”“梯几而戴胜杖”,“胜”可能是纺织用的玉轴,绾戴在头发上,象征着西王母作为大母神,调节万物的权威。所以看见戴胜鸟,就会想起西王母。七月初七,晚霞里,喜鹊们倾巢而出,赶去为牛郎织女架桥相会的时刻,用发簪划开银河的西王母,给小儿女搞完恶作剧后,可能就化身为戴胜鸟,与她的东王公一起,在田野里散步呢。这的确是她的田野,女性的、身体的、子宫的,生养与收纳万物的田园;她开辟了田园,守护着田园,以前在这里,现在也不会展翅离开。所以我觉得父亲与母亲,之前也应见过戴胜鸟,只是从前求温饱的年代,我们向田园求索着实用的利益的一面,并没有闲暇去关切它的诗意与神性。
我们大概是被这两只亲切良善的戴胜鸟目送着走到村口的。村子里荡漾着晚饭的香气,村巷中的太阳能路灯,正是在我们走上保刚家门前土坡的时候,兀然亮起来的。
2022年2月9日,孝感市农四村
早早地吃过晚饭,我跟父亲、母亲出门散步。六点多钟,太阳刚刚落土,天还没有擦黑,往西的水泥路,南边左手是正在拔节的小麦,已经高过了膝盖,北边右手是油菜地,繁花渐落,露出猫须般嫰绿修长的果荚。田野中的小枫杨树,珊珊可爱,枝柯上也绽开了勃勃紫芽,树下田地里有布谷鸟在咕咕咕地吟咏。东南风吹在手脸上,挟着土膏与青草的厚味,已经没有了寒气,母亲穿着早上姐姐骑电动车送来的新外套,大步向前,我在中间,举着我的登山杖,防备母亲畏之如虎的乡村田园犬。父亲跟在最后,刚才喝了两小杯白酒;妹妹村里作坊酿出来的谷酒,他赞不绝口,也不敢多喝,查出糖尿病后,他戒了烟,酒还可以尝尝,但超过两小杯,就会被母亲、姐姐、妹妹一起念紧箍咒。
父母离开乡下,移居南宁我弟弟家,已经有十五六年了,他们渐渐习惯了广西删除掉炎夏与寒冬的温和气候,每年也只是在清明节前,候鸟般回来祭祖、探亲,小住半个多月,然后在绿叶成阴子满枝的谷雨天里,坐高铁回程,继续接送心心念念的两个孙子上下学,吃早、中、晚饭。
父亲是泥瓦匠出身,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他的房子。二〇〇三年,祖父去世后,父亲亲手盖的三层楼的新房,而今也有二十年了,屋顶漏水,门窗有缝,地板砖开裂,都够他忙上好几天的。然后是西边没有拆掉的一间旧瓦屋,之前是祖父、弟弟与我的卧室,外墙与屋顶上缠满了枯萎的南瓜藤与我未及摘下的老南瓜,他忙着扯藤子,撑木桩,直到确信接下来的一年,旧房子安全无虞,不会在他无法监管到的狂风暴雨中垮掉。还有茅房边他种下的毛竹,由春韭般的一小簇,已经发展成参天立地的偌大一蓬,他要沿圈砍掉一些送给隔壁槐如大伯做扁豆架子,不然,竹枝迟早会戳到前面艾清家的屋瓦。今年他砍竹子的时候,还在茅房顶上发现了一小窝逃逸分群的蜜蜂,里面有蜂王,他用旧衣裳将它们裹到三楼阳台下,专门找出一只木箱给它们安家。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蜜蜂们正在阳光里绕着我们的房子嗡嗡营营诶。对,他由杂物间找来的木箱,红漆斑驳,改屋时舍不得扔掉,就是早年他结婚时,由母亲娘家陪嫁抬来的衣箱。
母亲也忙。村里老太太们“嵌五星”的麻将牌场,“上大人”的纸牌场,这些“召唤结构”已经期盼她有一年了,我弟弟的远程指令是“只能输不能赢”,但母亲哪里肯轻易认输,总得有一周左右的比试,才能勉强接受功力荒废、技不如人的残酷现实。好在牌场也是龙门阵,老太太们在淡定地赢钱的同时,也会将村子里的八卦一五一十地补课给母亲,母亲回到家,再转告父亲,这样他们两个,就可以将“我们村的新鲜事”同步更新一遍。
牌场竞技之外,母亲的社交活动也安排得很满。去姐姐、妹妹家做客,不然带回来的新外套,不就要锦衣夜行了吗?去肖港镇看望舅舅一家人,教舅舅用微信发语音,给舅妈演示她新学会的健身操与广场舞,嘱咐我在镇上开歌厅的表弟“走正道”,这大姐大的气场诶,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母亲还联系到了我外婆娘屋的一些表兄妹们,其中有一位名叫双珍的表妹,公社时代的闺蜜,隔了近四十年后,她们又重新见面,两位七十出头的老太太手拉手,眼神热烈、兴奋,还有一点紧张与羞怯,就是杜甫诗里面“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场景的再现。
父母的长辈差不多都已谢世,只余一位母亲的姨妈,是外婆的小妹,嫁到我们村,住在村北,小时候我们叫她“北头姨婆”,父亲与母亲结婚,是她做的媒。她已经近九十岁,身体还硬朗。看望姨婆,是母亲社交活动的顶点。姨婆有养老补贴,不生病,花不完,所以坚决不要母亲给钱,母亲知道老人家爱吃蹄花,会清早去涂河集,买三四斤重的猪蹄髈,由父亲负责用斧头剁好,清理干净,然后两个人一起送去姨婆家。这时候,父亲会脱掉他砍竹子搞蜂子的工作服,换上呢子外套,洗脸梳头,神情里就有一点女婿去见丈母娘的忸怩。姨婆之前做过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举手投足有《红灯记》里李铁梅的气概,现在音容笑貌,是越来越像外婆了。外婆去世也有二十年,小脚,吃斋,不识字,晕车船,在世时,清明谷雨,父亲会用板车载着她,来我们家做客半个月。
如此时此刻这般,跟随父母在乡间散步,并非容易。父母尚在,身体尚好,能远游归来,能有一点闲暇与兴头,这个是前提。
散步的概念,与广场舞一样,也是最近才由城市传递到乡村来的。村庄与田野之间的大路、小路、沟渠、田埂,来龙去脉,我们像自己的手掌一样熟悉,出门,回家,往返作息,行走在路上,肩挑手提,冲风冒雨,热汗淋漓,是去做事,求温饱。大概也是最近,我们才能将这些道路当成闲逛的场所,鼓腹而游,去聊天、养生与消食。
父亲与母亲是在南宁的小区里形成的“惯习”,眼下村里人晚饭后出来荡路的,三三两两的也不少,大概是肖港镇里传来的时尚吧。
我们遇到后头屋的聋子婆婆,一个人背着手,稍伸着脖子,往前走,与母亲比划着呀呀讲话,她大概可以盯着嘴唇读懂一些字词,自己发出来的声音,好像也越来越清楚了,她要母亲去她的菜园里摘菜,她种的土莴笋已经可以开园了。槐如大伯慢慢追上父亲,沉默地抽着烟,父亲戒烟好几年了,自然是又要向大伯唠叨抽烟的危害,不久就将话题转向如何量血压,前几天他送了一支血压计给他的堂兄。大伯八十岁,目前是我们村辈分最高与年纪最长的男性,一周后我送父母回南宁,父亲降下车窗与槐如大伯告别,大伯站在他家门口的桂花树下抹眼泪。我还看到邻村肖家河的一位大姐,坐着轮椅与我们打照面,她已经认不出父亲与母亲了,但我认得她,小时候,我去初中学校读书,会由她家门前经过,她因为小儿麻痹症,常常望着水井旁边发呆,像孔乙己一样背着麻绳坐在一只稻草蒲团上。后来她得到了轮椅,现在她手动的轮椅已换成电动的,沿着乡村新修的水泥路,可以毫不费力地回村去。我想,再过几年,外骨骼机器人的技术完全成熟后,这位大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乡间漫游了。
向西三五百步,走到十字路口,聋子婆婆与槐如大伯掉臂回村,我们三个折转向北,沿着汪寺公路继续朝前走。大路之西,澴河之滨,晚霞之下,沿着路下的沟渠展开的,是我们村一百多亩稻田,我们家的三四亩责任地,也在路边,方方正正,与其他的稻田一样,长满马鞭草与紫云英。稍远的澴河堤下,我一位远房堂兄保志,正开着他朋克味十足的新拖拉机翻地,保志嫂站在不远处的田埂上,看样子是来催促他回家吃晚饭。保志的父亲外号“黑人”,生产队的时候,他管我们村的抽水机,现在,保志与保志嫂几乎接手了全村所有的水田,各自开着各种农机,宰田,上水,插秧,打药,收割,脱粒,这是从前全村两百多男女老少的活儿,他们两个打理得不慌不忙,只是晒得黢黑,真正是接下了黑人大伯的班。等等,保志哥黑炭一般倒也罢了,保志嫂从前可是塆里的一枝花啊。这些水稻田里长的粮食,养活了我们祖祖辈辈无数代人。父亲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四个在路边责任田的泥水里劳作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清明谷雨办好田,立夏小满正栽秧,我插秧割谷,水平都远不如姐姐妹妹,水田里泥鳅鳝鱼不少,蚂蟥蛐蛐也很多,夏天雷雨,水田下沟渠里水流如箭,正好用小挡网捉小鱼小虾,在小木桶里活蹦乱跳。
向北走一二千步,是匡埠村,母亲停下脚步,她已经听到了村口狗子的龇牙腹诽,一脸惊惶。我们转向东,再向南,沿着蔡家河与我们村田畈中的小路往回走。匡埠村正在请来挖土机大兴土木,他们想将村东一连串新月形的池塘清淤贯通,筑成一片花园。父亲说,这些池塘向南,一串一串,断断续续连着蔡家河、郑家河、魏家河、官家河、涂家河,从前是澴河的旧河道。到底有多从前呢?父亲说他也是听祖辈讲的。柳宗元到南方,学到本地的词语,他写《永州铁炉步志》,说“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这个“步”,大概就是匡埠的“埠”;又写《袁家渴记》,说“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为‘渴’,音若‘衣褐’之‘褐’”,大概也通蔡家河、郑家河的“河”吧。所以由地名来看,我们耕作在周南汉东,澴水之滨,云梦泽陂,“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有千百年,其间山陵倾倒,河流改道,也是有的。
我们村的墓地,就在这条旧河道东边,蔡家河与郑家河交壤的一片龟背地,当日应可向西俯看老澴河的一弯清流,再往东三五十里,就是大别山的列列青峰。祖父祖母葬在其中,前几天我们来放了鞭炮,烧了纸钱,伐去了坟头的构树苗与坟间的野蔷薇藤。我们路过的时候,惊起坟林枫杨、构树与杉树间的鸟儿,麻雀、喜鹊、斑鸠,叽叽喳喳,翕动翅膀,又重归平静。
小路旁,纠缠的野豌豆丛中,还有不肯归巢的鸟儿,我认出来,是一对戴胜鸟。扇子一样的羽冠,船钉一样的长嘴巴,云霞一般灰棕色的羽翼间,还有白色的条纹,眼睛黑豆一般闪动,它们并不怕人,也不担心天黑,不紧不慢地走在田埂上,翻找草丛中的蚯蚓与蝗虫。它们不爱展开双翅高飞,用双爪走路还多些,来到庄子的《逍遥游》里,既不是斥鴳,也不算鲲鹏。这并不是我在乡村第一次看见戴胜鸟,去年夏天路过殷家大塆,在村后的河堤上,也看到过一对,它们好像遇到了兴高采烈的事,扑扑扑地叫着,颈部前倾,不停地点着头,头上的羽冠耸立怒发,有一点像公鸡的冠子。栎树兄跟我讲,在魏家河一段的小河堤上,他也遇见过一窝。可见它们各自是一对戴胜鸟夫妇,捉虫养育孩子,将家安在各种树洞或者河堤的夯土洞里。每一个戴胜鸟的小组,可能都被上天安排有一块巡视与作息的小小田园。这些年来,乡下的鸟,种类与数量都在变多,黑背喜鹊、乌鸦、大雁、白鹭、野鸭,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陌生的鸟儿,是从前我们的田野里没有的。我问母亲以前有没有看见过戴胜鸟,母亲先说看到过,之后又有一点犹豫不定。父亲说这鸟的羽毛颜色就像母亲的新外套。
我读《山海经》,讲到西王母“蓬发戴胜”“梯几而戴胜杖”,“胜”可能是纺织用的玉轴,绾戴在头发上,象征着西王母作为大母神,调节万物的权威。所以看见戴胜鸟,就会想起西王母。七月初七,晚霞里,喜鹊们倾巢而出,赶去为牛郎织女架桥相会的时刻,用发簪划开银河的西王母,给小儿女搞完恶作剧后,可能就化身为戴胜鸟,与她的东王公一起,在田野里散步呢。这的确是她的田野,女性的、身体的、子宫的,生养与收纳万物的田园;她开辟了田园,守护着田园,以前在这里,现在也不会展翅离开。所以我觉得父亲与母亲,之前也应见过戴胜鸟,只是从前求温饱的年代,我们向田园求索着实用的利益的一面,并没有闲暇去关切它的诗意与神性。
我们大概是被这两只亲切良善的戴胜鸟目送着走到村口的。村子里荡漾着晚饭的香气,村巷中的太阳能路灯,正是在我们走上保刚家门前土坡的时候,兀然亮起来的。
2022年2月9日,孝感市农四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