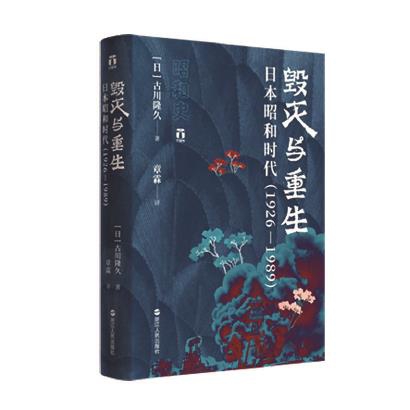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1-08-25 第26,967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用理性和良知书写真实的历史
——读古川隆久《毁灭与重生》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姜建强最近,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历史学家古川隆久《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日语原版书题为《昭和史》,筑摩书房2016年)。当准备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笔者闪过一丝疑惑:为什么要翻译出版这位1962年出生的中生代学者的昭和史?论知名度不及史家保阪正康的《昭和史的教训》 (朝日出版社),论畅销度更不及史家半藤一利的《昭和史》(平凡社)。但开始翻页阅读,笔者便被作者的学术真诚和学术勇气所吸引。花了几天时间慢慢读完后,感觉这本书最具意义的是没有迎合被司马辽太郎调养而成的日本读者的口味,更没有为复苏历史记忆而放弃历史的真。与日本各种版本的昭和史相比较,笔者以为古川的这本昭和史显然是理性的一个高度,良知的一个高度,当然更是生命本真的一个高度。
如何防止历史失败主义者的产生
所谓昭和史,就必然涉及到那场侵华的“15年战争”。对那场战争的被害国和被害者来说,日本和日本人毫无疑问就是罪恶的加害者。若遵循一般战后处理方式,用其真诚的“忏悔”以及政治家虔诚的“道歉”,或许就能清理完历史情感。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尤其是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以及不分昼夜的东京大空袭,日本人所遭遇到的凄惨痛楚和死亡,使得他们在感觉和感情上总以为自己也是“被害者”。这正如历史学家加藤阳子在《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中设问:为什么日本人认为自己是“被害者”呢?理由之一,加藤认为是“国家甚至无法告诉阵亡士兵的家属,这些士兵是在何时、何地失去了生命的”(参见第304页)。
当然,这里的逻辑前提不能被颠倒——被害者就是被侵略者,加害者就是侵略者。问题是即便是加害的侵略者——日本人,国民情感的积淀也会构成战后日本的一个集体历史记忆。难度在于这个集体的历史记忆又不能面对被害国被害者的“被害记忆”。如何处理这段集体的历史记忆,也就是如何理性地书写这段战争的昭和史。由于复杂的历史记忆(如原爆记忆、大空袭记忆、满洲逃离记忆等)不能明言,那么势必就会在历史书写中以最危险的方式完成对过去的否定与曲解,呈现出另一种可诅咒的荒唐事和可恶人。于是我们读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日本学者写的昭和史,虽然对本国的国民情感有了个温存有了个缓冲或者有了个寄托,但对被害国被害者来说,可能又是第二次第三次或第N次的被害。这就像随着纪念碑和纪念馆的建立,死者的表象也就成了历史表象的一样。如果说历史的重复性是讲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惯性,那么历史的重演则是人世层面的问题,一定是人的判定受了当下视角与在场的影响。但历史又绝非单纯地作表面的循环。当人们还处在这不是“似曾相识吗”的表象意识中时, “再来一次”的凶险度要远远超过原发状态。这也是历史的可怕之处。所以,这也是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们再三警示善良人的一句话: “人们呀,我是爱你们的,可你们要警惕呀。”但后人往往是历史的失败主义者。
如何防止历史失败主义者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工作程序就是史学家们要守住底线,书写真实的历史。这也是我们读古川《毁灭与重生》的价值所在。
日本历史研究的所谓“红线”
先看看古川对侵华战争的书写。比如书写南京大屠杀,这是古川昭和史最为亮眼的地方。在第三章“战争年代:1937-1945年”中,古川干脆就用“南京大屠杀”的文字作为小标题来加以论述。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以后, “最终,仅仅是下笔书写就会令人感到难过的惨剧发生了”。这里,古川毫无掩饰地写上了“30万人”的数字。他这样写道: “占领南京的日军至少屠杀了数万名中国军人和平民,如果算上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发生的事件,那么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总数可能达到30万人,这就是南京事件,也被叫做南京大屠杀。” (122页)古川最终能将“30万人”的遇害数字写入自己的历史专著,在当今的日本史学界堪称第一人吧,其意义绝不可低估。
如果说日本的历史研究也有所谓红线的话,那么南京大屠杀的遇害人数就是一条心照不宣的红线。翻遍在日本出版的各种昭和史著作,大多用“南京事件”的文字来加以处理,连“南京大屠杀”这几个文字都隐而不宣,更不用说写入“30万人”的遇害数字了。如在日本有昭和史研究第一人之称、今年1月去世的历史著作家半藤一利,于2004年2月出版的《昭和史》 (平凡社)第六章中,他论述“卢沟桥事件”和“南京事件”,对后者起的小标题是“确有‘南京屠杀’,但是……”半藤想“但是”什么呢?虽然日军进入南京后有“大量的‘屠杀’和各种非行事件的发生”,但是, “像中国所说的屠杀了30万人,以及在东京审判时也这么说,那是不可信的说法”。半藤的学术油滑在这里显现无疑。与古川相比,良知的高下顿然分明无比。还有专攻日本近现代史的学者秦郁彦,他早在1986年就著有《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 (中央公论社)一书。在“大 屠 杀——否 定”与“30万/40万——虚构”的构图中,他还是选择了后者。他甚至嘲讽中国人素有“白发三千丈”的艺术夸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取“4万人”遇害说。虽然他也认定当初日军在南京的各种“大量屠杀”是不可撼动的事实,对此“作为日本人的一员,向中国人民深深致歉”。他还坚信, “如果没有这种认识,今后日中友好就无从谈起” (同上书244页)。不过秦郁彦在另一本《阴谋史观》 (新潮社2012年)中,记述在南京陷落前的12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也好苏联也好都以中国为战场,所能想象的就是中国成了牺牲品。” (同上书172页)。这里,秦将这个问题技巧地搭上了苏联,想以此表明这并不是日本的孤立现象。
以笔者所阅来看,在日本,堂堂正正不加掩饰地说出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为30万的,一个是历史学家古川隆久,一个就是小说家村上春树(参见《刺杀骑士团长》)。当然,有人会说,数字总是冰冷的总是抽象的,拘泥数字就冷落了历史情感,淡漠了个体生命的鲜活。但问题是,历史研究就必先给出数字,先给出抽象,然后才能具象化鲜活化。如首先要有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个数字,首先要有日军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个数字,然后后人才会在阅读历史,在震撼、在惊叹这个数字的同时,唤起一种不可抑制的历史情感,自觉地去一点点、一丝丝、一段段、一片片、一个个地追寻历史真相,以警示后人历史悲剧不可重演。而古川所做的就是这么一份工作。
不再暧昧不再含糊不再轻飘的历史
总结古川隆久的历史书写,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用一种“一目了然”的笔法,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让历史变得不再暧昧、不再含糊、不再轻飘。这种笔法虽然也多少牺牲了历史特有的丰富性与不确定性,读起来有时不免枯燥干巴,但还原的却是真实的历史情感与历史记忆。对作为战争的被害国被害者的我们来说,阅读古川的《毁灭与重生》,有一种“解馋”之味,有一种迟到的舒然感。只可惜,这样的历史学者在日本太少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日本,随着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代渐渐消失,一个危机也随之出现。那些对灾难性战争没有恐怖记忆的人,也许会曲折地进入相似的危险领域。 “重蹈覆辙”的历史哲学之语就是“历史重演”。所以,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古川隆久这样不断向后人敲警钟的学者。
2010年去世的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曾期待日中学界有一种“知识共同”的形成。笔者以为《毁灭与重生》这本书,就是一种努力和结果。这本书能及时被引进出版,也显现出一种视野与智慧。而中国读者读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知识共同”的共享过程。
(作者系旅日文化学者,曾在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担任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