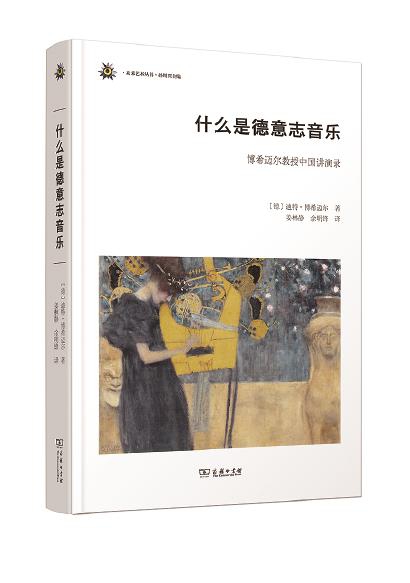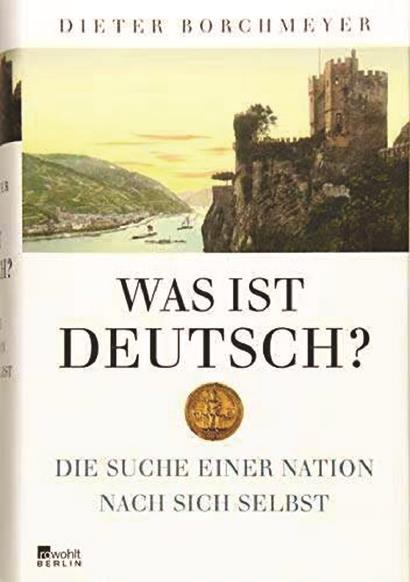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1-07-03 第26,914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从德意志音乐看文化爱国主义
庆祝贝多芬诞辰,德国波恩街头用其肖像壁画装饰一新 视觉中国
■余明锋“识别德意志人的标志是,在他们那里‘什么是德意志’这个问题从未消停过。”(《善恶的彼岸》,第244节)撇开尼采的批判意图不论,这句妙语着实切中了要害,可谓德意志自我认识的绝佳概括。
德意志反思的广度:音乐也能塑造民族认同?
人们常说,德意志是哲学的民族,这指的无疑是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曾诞生其间。从康德1781年出版《纯粹理性批判》到黑格尔1831年去世,仅就这50年来说,德意志的精神世界已然群星灿烂。可我们不妨借用尼采的揶揄,为“哲学的民族”增添一层含义:这是一个勤于自我认识,可也因此一直为自我认同倍感焦虑的民族。就此而言,其民族性中就蕴含着一层浓重的哲学反思意味。
有趣的是,这个自我认识的德意志故事不仅与哲学史有关,而且还与音乐史有着紧密的关联。《什么是德意志音乐》一书主要就是谈这样一个“音乐与德意志的自我认识”的故事。从巴赫到贝多芬再到瓦格纳,这些划时代的音乐家及其伟大作品无疑有着显著的德意志品格。可音乐这种最为抽象而普遍的艺术语言何以参与了一个民族的身份建构?如何塑造了德意志的自我认同?
作者博希迈尔是著名日耳曼学家、海德堡大学荣休教授,曾任德国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院士、主席,他还曾任西门子音乐基金会顾问委员会主席。作为深通音律的日耳曼学家,他的瓦格纳研究建树尤多、影响尤其广泛。此书对于“什么是德意志音乐”的回答虽然仅仅截取了几个断片,但背后实有一种清晰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整体看法。原因在于,作者在2017年刚出版了一本题为《什么是德意志》的巨著,用1056页的篇幅对这个问题做了空前系统的梳理。书中的第十章以“德意志音乐的范式”为题,专论德意志认同的音乐故事。这片波光因此不只是断片,而且是对全景的一次折射。
文化爱国主义:先有文化认同,再有民族认同
研究德意志思想和文化的学者常常谈论德国哲学史、德国音乐史、德国艺术史和德国文学史等等,可直到1871年,俾斯麦的普鲁士打赢了普法战争,统一了德意志诸联邦,德国才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存在。 “一个德意志的民族国家对歌德和席勒而言是无法想象的。”博希迈尔尤其聚焦于席勒来说明这当中的转变。席勒与歌德深入交往的十年,开创了德意志文学的古典时期,构成了魏玛文化的核心。民族国家的缺位,恰恰使得这一时期的德国文人能够以一种启蒙主义的普遍历史观来看待自身的文化使命。博希迈尔指出,这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历史原因,从1795年《巴塞尔合约》签订到1806年拿破仑入侵,魏玛赢得了十年和平,这十年才为魏玛的世界公民文化提供了空间。不过,早在拿破仑的军队入侵之前,1801年的诗歌残篇《德意志的伟大》已然表明了席勒的转变。事实上,从拿破仑1799年担任第一执政开始,像费希特这样狂热的法国大革命支持者就带着疑虑的眼光在关注局势的变化了。
“拿破仑的崛起就带来了一个转折,这是一种‘从对欧洲抱有希望的高昂情绪跌落到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爱国主义’的转折。”殊为有趣的是,这种“文化爱国主义”的灵魂仍然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的躯体。所以会有“文化民族”和“国家民族”的区分,这是一个先有文化认同再有主权国家的民族,一个先有灵魂再创建躯体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这种分裂,时任巴塞尔大学语文学教授的尼采才会在1870年先以医护助理的身份入伍,随后又担心德意志文化毁于普鲁士的成功。 “文化民族”无疑有着创建“国家民族”的热望,可一旦灵魂获得自己的身体,它是否能够支配身体还是反被身体支配,就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尼采预感到, “文化民族”将衰退于“国家民族”的胜利。
无论如何,德意志的民族认同感首先基于那种与“文明”相区别的“文化”概念。文明指政治、经济和技术等社会现实,略相当于黑格尔所谓“客观精神”的领域,英法文明彼时遥遥领先;文化则指思想、艺术和宗教等,略相当于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的领域。绝对精神是目的自身,凌驾于客观精神至上,彼时无能于政治的德国人于是在文化中找到了政治的高贵替代物。 (参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音乐何以能与哲学一道构成德意志的自我认识,也就并不奇怪了。
进一步,这种“文化爱国主义”养成的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使命感的选民意识。这种从政治无能所造成的民族苦难中升华出来的选民意识,与尼采在《敌基督者》中所揭示的《旧约》的权力意志逻辑,有着惊人的相似。尼采称之为“怨恨”。熟读尼采的托马斯·曼在《试论席勒》中曾触及这种怨恨—升华的逻辑,他的朋友卡勒(Erich von Kahler)更是直接将这种逻辑追溯至《旧约》。博希迈尔如是总结他们的分析: “‘不幸的翻转’促使‘向更高处的提升’,引起一种‘被拣选’的感觉。这种预言只会‘在受苦难的民族中’出现; ‘自以色列民族以来,先知先在德国,后来又在俄罗斯出现’。”包括音乐和哲学在内的文化使命可谓德意志的信仰。这也让人联想起黑格尔,当《法哲学原理》最后把德意志人规定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后的世界历史民族时,他其实继承了席勒: “对于席勒来说,德意志民族是个末世论民族,德语是世界语言,末世语言。”
德意志音乐如何被刻画为“灵魂”而形而上学化
除了哲学史上的黑格尔,席勒的世界历史选民意识还有一位至关重要的继承者,那就是音乐史上的瓦格纳。可音乐也能像诗歌和哲学一样说德语吗?德意志音乐何以成为“德意志身份的阿基米德支点”和“一个文化民族的合法性神话”?
博希迈尔总结了两种音乐德意志性叙事。“第一种认为德意志音乐的特殊性在于其深刻性与缜密性,德意志音乐也由此与意大利(或法国)音乐区分开来。其中最重要的对立就是‘和声’与‘旋律’之间的对立,前者是德意志音乐的主要标志,后者则是意大利音乐的主要标志。这种对立背后的原因是声乐在意大利的主导地位及器乐在德国的主导地位。”在德意志音乐崛起之前,意大利人才是欧洲第一流的音乐民族。那时候,声乐和旋律也才是第一位的音乐要素。植根于浪漫主义的德意志音乐美学决定性地抬高了器乐和和声的地位,提出了“绝对音乐”的理念,其与非德意志音乐的区别被刻画为“灵魂与感官”的二元对立。
“绝对音乐”的理念实可追溯至霍夫曼(E·T·A Hoffmann)1809年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所写的乐评,可首先引入“绝对音乐”概念的是瓦格纳。有趣的是,瓦格纳意在创造“整体艺术作品”,独立于声乐的器乐之为“绝对音乐”,因此是他的批判对象。首先正面运用这个概念的其实是瓦格纳的敌人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而瓦格纳则在深入阅读叔本华之后,接受了浪漫主义的音乐美学,才重估了“绝对音乐”。德意志音乐由此成为了通达“本体界”的形而上学语言。
第二种叙事则认为德意志音乐具有“混合品味”,是吸收了意大利和法国的不同元素综合而成的。第二种模式显然更具包容性,可瓦格纳在《什么是德意志音乐》中恰恰由此论证,德意志音乐由此体现了“超越一切民族束缚和限制的‘纯粹人性’。”德意志音乐的根源是民族的,目标则是世界的。于是,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德意志音乐都成了世界历史选民的形而上学之声。
世界的共同价值需要各民族的自我认识契机
重温这一段“音乐与德意志的自我认识”的故事,令人不禁发出唏嘘之叹。寻求共同价值本是一个民族崛起之时合乎历史大势的自我要求,只有如此,民族的才能成为世界的,才能真正贡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即便再伟大的民族,一旦落入选民意识,都会陷入巨大的危险。有关于此,我们不妨补充一则逸闻。社会学家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中讲了一段他父亲亲身经历的音乐往事。1945年,德军侦查部队转播了一段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飞行员们立即前往维也纳,因为这座城市为《玫瑰骑士》提供了背景。可许久过后,他们才想起来,德累斯顿才是真正的目标,因为那是《玫瑰骑士》的首次公演地。他们立即转飞德累斯顿,可已经来不及阻止盟军的飞机。这则逸闻充分说明了文化民族的艺术水准,可也成了其现实命运的绝佳脚注。
自我认同之于一个民族,犹如自我意识之于个体, “我是谁”的追问往往也是根本上的自我塑造。以史为鉴,哲学民族曾经的自我误识,也是各民族自我认识的契机。
至此,我们大约可以理解博希迈尔重提“什么是德意志”这个瓦格纳式问题的用心所在。时过境迁,博希迈尔显然不是要通过德意志音乐重新召唤错误的选民意识,而是要敦促不断的自我认识。一个健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赖于世界各民族的自我认识和彼此认识。
(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